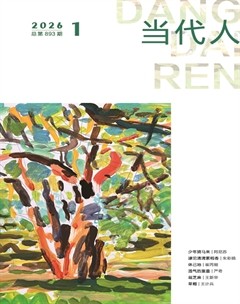回村之前,我给天津的堂兄打了一个电话:“哥,你在天津,还是在村里?”
堂兄说:“我在村里呀,该我照护你大爸了。”
我心头一喜,终于有机会在村里与堂兄相遇了。
我与堂兄交流,基本说的都是村里的方言。我们是山西晋南人,晋南的方言五花八门,十里八里地的距离,方言却是千差万别。我们都是从村里奋斗出来的,上大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他在天津安家,我在北京落了户。他是军人,正团职退役,我是文人,从事编辑工作。一文一武,也是有趣。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家乡的话,而且说得非常纯正,流利。
比如说照护一词,实际上包含了照顾、陪伴、陪护、照料、护理种种含义。但无论用哪一个词,都没有照护一词更亲切,更丰富。无论是晚辈对长辈,长辈对晚辈,还是朋友相托,或者生人与熟人之间,照护一词都适用,有关照与呵护之意。
我和堂兄都是六零后。他兄弟姊妹四人,我家也是。他排行二,我排行老大。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家三四个孩子,基本是乡村人口的标配。我大爸,亦即大伯、伯父,也就是他的父亲,今年九十有三,是几千人的村里的寿星,非常令人惊奇的是,他吃得好,睡得香,除了耳朵背一点之外,身体没有别的毛病。大堂兄笑嘻嘻地对我说过:“哎呀,你大爸每一顿吃两个馒头,饭量比我还大呢。”
老人生活虽然能自理,但毕竟年龄大了。所以,他们兄弟三人分别轮流照顾大爸。本来,一人一个月,老大和老三在村里,方便,但堂兄在天津,如此频繁奔波,非常辛苦,所以,他一回村,索性照顾四个月。遗憾的是,每次我回村,都与他失之交臂,几乎没有碰过面。这一次,我们可以在村里相遇了。
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他一个人在村里待四个月,是如何度过的。大爸九十有三,他也六十有三了。我想,孤独和寂寞是少不了的,重要的是,种种的不习惯不适应难以启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偶尔通电话,他会爽朗地大笑:“没事干吗?给你大爸做好一日三餐之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余的时间干什么呢?小学、高中同学倒是不少,但人家在他这个岁数,还在田野上忙碌呢,他是个退休人员,是个闲人,也不好占用别人的时间。再说,交流也有障碍,谈什么呢?村里同学谈谈收成,农活,他可以聆听,但他若谈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或多或少在对方的眼里都有炫耀和矫情的意味。毕竟,不在一个频道上,交流起来非常的麻烦。
堂兄的孤独与寂寞,我很理解。这种感受,几乎是所有从乡村奋斗到大城市的人共同拥有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几乎都不用说什么,彼此只是爽朗地大笑。痛,无奈,脆弱,敏感,苍白,苦涩,五味杂陈的元素,都在笑声中纷纷扬扬,犹如夏天在麦场上扬场一样。
先前,我是给他寄过一箱书的,供他在四个月内闲读。我想不到更好排遣寂寞和孤独的方式了。我这份小小的体贴、关心,他是清楚的,能体会到的,毕竟,他大学学的心理学专业。
一回到村里,我就迫不及待去找他了。他家在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在村里的主干道上一走,童年的往事就纷至沓来了。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又那么陌生。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但映入视野中的一切,却是陌生的,每次回村,都有初来初到初见的感觉。乡村变化太大了,完全城镇化了,尘土飞扬的大路和破旧的房舍全都无影无踪了。
进了堂兄家的大门,就看见地上一根长长的电线,从门口直通院子中心。院子中心,放着一台洗衣机。看样子,辛苦的不止堂兄,还有这台洗衣机。大爸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大解小解哪有那么干脆利落的,或多或少,总得留点尴尬的痕迹。倒是这洗衣机,慷慨大度,毫不介意。我仿佛听到它在豪情万丈地说:“小菜一碟!”
“回来啦!”堂兄说。我们相视一笑。我凝视着他的脸,观察着他细微的表情变化,以及皱纹里隐藏着的秘密。小说里的细节,就是这样被挖掘和被展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