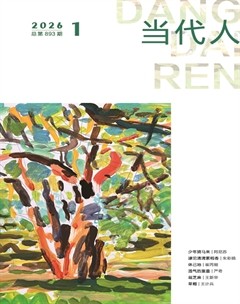在当代文学的体裁光谱中,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差异,甚至比小说与诗歌的分野更为巨大。短篇小说创作与诗歌创作拥有着诸多的共通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两者都是在极小空间内“戴着镣铐”的舞蹈。这也就注定了虽然短篇小说貌似与中长篇同属小说这一阵营,却在结构构建和审美趣味上展现着截然不同的艺术面貌。短篇小说的字数限制犹如一个“紧箍咒”,它逼迫着作者绞尽脑汁去提高文字的表达效率。中长篇作者思考中的冗余和闲笔,在短篇中完全有可能是败笔的可疑。这一点上,短篇小说同诗歌完全一致,一个多余的段落会导致“短篇”作为结构的整体性崩塌。也就是说,“爆发力”,这种宝贵的文学品质,在短篇小说中是必备的基本的能力,如果不能完成“寸铁杀人”的艺术冲击,写作者就会即刻被“短篇”这一结构反噬。当下大部分文学刊物,短篇小说的比例构成一般都是相对保守的,对作者更加“温和”“友好”的中篇小说更容易受到喜爱,而在面对短篇小说的“紧箍咒”时,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会格外审慎。
于是,这个“紧箍咒”让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刊发对象的刊物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就是选稿的挑战。短篇小说的“好”需要符合诸多维度的定义,但它的“差”可能只需要叙事中的一处失误即能成立,如何在海量的稿件中找到藏身一隅的好短篇,某种意义上是对刊物编辑的一种“折磨”。第二是培养读者的挑战。短篇小说的发力点往往藏在文字不显眼的褶皱中,长期浸润于长篇叙事或快餐阅读的读者,容易陷入短篇结构带来的阅读障碍。什么是克制?什么是留白?什么是张力?以短篇为主的刊物,在培养固定阅读群体的过程中,势必要做出更为长久的努力。第三就是培养作者的挑战。新手极易陷入“短篇是中篇或长篇缩写”的误区,在创作中用情节替代细节、用密度替代深度、用宏大替代微观。在培养作者的过程中,编辑需要竭力帮助他们建立对短篇小说独特逻辑的认识,同时更需要帮助他们克服在建立认识后对短篇这一结构的恐惧,这一点相较前面两点更为关键,同样也更为困难。
2025年,《当代人》依然延续了刊物独立的风格,发表了近50篇短篇小说,有力回应以上的挑战。这些作品涵盖了现实主义、奇幻叙事、地域书写等多重维度,其作者既有深耕文坛多年的成熟作家,也有刚露头角的青年新锐。从整体风格看,这些小说成熟与成长共存,通性与差异共存,它们在风格各异的讲述中,在水平线之上呈现了较为一致的审美趣味。它们不仅彰显了短篇小说独特艺术品质,也折射出了《当代人》在刊物风格塑造与作家群体培养中的自觉追求。
短篇和故事
谢有顺有一篇评论的题目很有趣,叫作《一个好作家可以不讲故事,但他必须会讲故事》,他在文中谈及了“先锋主义”之后中国当代小说的某些困境或者歧途,他认为,“一个渴望标新立异的人,可以成功地扮演形式先锋,但面对故事这个古老的形式时,他往往会露出马脚。一味地指责读者缺乏阅读训练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有理由对一个小说家提出故事上的期待……几乎一切伟大的作家都讲故事,至少他们能讲故事。”小说当然非单纯的只是故事,小说家当然也不是只需要做好讲故事这一件事,但需要讲故事又讲不好故事,就是小说中灾难的开始。小说阅读中一个通常的认识是“短篇小说写场景、中篇小说写故事、长篇小说写人物”,乍看上去短篇仿佛不需要讲故事——这是大错特错的。对小说家而言,短篇小说的形式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智力的游戏,而故事作为内容核心才是叙事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短篇“写场景”是叙事展示的一种形式,高密度、高强度、高提炼度的叙事——或者说讲故事——的过程才是达成“写场景”的通途。
李延青的《谁心里都有神圣的地方》是“会讲故事”的典范,作者将一段跨越一生的友情与一场迟来的爱恋,淬炼成承载着人性重量与时代变迁的文学文本。小说的故事线索十分清晰,农民企业家小黑晚年想与县剧团名角银铃儿结伴,托付发小王建民说媒,银铃儿婉拒并不久后因肺癌离世。王建民在葬礼结束后一句“省了口棺材”的玩笑,让相交半生的两人彻底闹掰。若仅止于此,这只是一则关于友情与黄昏恋的市井故事,但小说通过密集的人物心理刻画与时代生活细节的展示,让“故事”升华为“小说”,抵达了更深厚的精神内核。小黑心中的“神圣之地”,正是银铃儿对他青春期的启蒙与精神信仰的守护,王建民的玩笑恰是对这份神圣情感的冒犯,这也是小黑无法释怀的核心原因,也构成了他人性中的复杂张力。同时,小说通过追溯两人的命运交织,勾勒出时代变迁的轨迹,与改革开放、环保转型等时代主题形成了共振。
李冬泉《黄土黄》中的故事遵循着一根更为明显的时间线,从讨饭的周平原因一炕山药干留下,到与大她二十五岁的男人成家,再到历经妯娌战争、积极谋生,最终为男人操办葬礼,以外来者的身份成为这个家的主人。小说叙事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周平原与二婶的“战争”,这场冲突的核心,是贫困年代家庭资源稀缺的现实,更是外来女性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反击。周平原后来织包袱时抽边的技巧更具深意,包袱首尾两端线数丝毫不减,中间却悄悄抽出十几根线,既保证外观合格,又省下棉线。这种小聪明当然是偷奸耍滑,但同时也是物质贫乏年代中国农村底层女性维护生计与尊严的智慧与无奈。
贺亮的《对手》则以冀中抗战为背景,在叙事中完成了“讲故事”的超越。小说的表层故事线是木匠宋继三被陈财主请去打家具,意外卷入鬼子斋藤的粮食抢夺与据点建设,最终独自猎杀斋藤的经历。木匠猎杀斋藤的过程,极具象征意味,他只是“举起绳索套在了那鬼子脖颈上,转身背在肩上往东就走”,动作朴实如平日扛木头,却因“想起了抗日而死的师傅和礼全”而充满情感重量。作者笔下的故事讲的是“木匠杀鬼子”,笔下的小说则是“抗战中人民群众朴素爱国情怀的觉醒”,故事成为人性的容器,侵略者的残暴、人民的反抗在细节中层层递进,小说也因此避免了抗战题材中常见的概念化书写。与之类似的是《金刚坐》和《落樱的天空》,两位作者在表面故事线下隐藏着或是“接受自我”的挣扎,或是异乡人的生存困境,同样实现了对“故事”的超越。
青年作家在关于科幻题材创作的探索中,则是陷入了某种讲不了故事的挣扎之中,如《梦旅人》《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