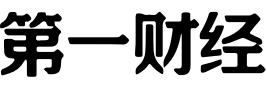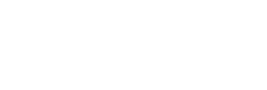现代人在嗅觉方面的退化,我自己就是一个例证。
2025年夏初,在汕头的小公园闲逛时,我邂逅了一家卖“老香黄”凉茶的药店。店门口立着一块KT板,上面的字密密麻麻,竟是十多年前蔡澜一行来此拍摄老妈宫,路遇此店,蔡澜极力哄说胃痛的导演喝下十年陈老香黄的轶事。蔡先生的广告做得有点多,我并不是全信,但那次我决定尝试一下,毕竟人家祖籍是潮汕。在镇定地“检查”过那坨黑乎乎的盐制佛手柑之后,我把一杯“十年陈酿”送到嘴边。结果不但口感极佳,而且周身神清气爽,不禁大呼过瘾。

后来想想,作为出生在“佛手柑之乡”的金华人,自己实在是个只会食指大动的糙人,过度依赖味觉。其实,我上中学那会儿,身边也没少见亲戚朋友家里种上一盆佛手柑闻香添绿的。它们还作为果供被香主们精心挑选,并小心翼翼地奉在南方各大寺庙佛龛神位前的供桌上。在曹雪芹笔下,作为大户人家的清供,佛手柑与米芾颜真卿的书法作品被主人一视同仁。在汪曾祺的高邮老家,其祖父在堆土造园时,在小山正面亲手种下4棵香橼树(佛手柑其实是香橼的变种)。以上种种,都在告诉我们,香橼(佛手柑)这种古老的植物,早已渗透从普通百姓到精英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
“ 香橼味道很冲…… 肉不能吃……”,汪曾祺不理解祖父为何要种“不是很受欢迎”的香橼。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些异于普通水果的“无用”特性,让香橼具备了某种神性,并与宗教产生关联。
迪亚蒙特与香橼海岸
香橼并非不能吃。我和意大利人Franco坐在迪亚蒙特小镇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吃完正餐后,侍者给我们端上来一款专门用当地特有的香橼制作的格兰尼达冰沙(Granita al cedro)。见证香橼的另一面宗教性,依然从味觉开始。
Franco在卡拉布里亚商会工作,之前在东南亚待了20年。他告诉我,这款甜品保留了香橼特有的苦味,是欧洲人的喜好。相对而言,东方人对苦味的耐受度要差一些。广东人懂得如何通过用盐腌制的做法驯服香橼强烈的气味,临近的印尼地区也有类似处理方法。Sukade—当地人用盐去除果皮上的苦味后制成的浅绿色半剥皮糖渍香橼果肉,被殖民时期的荷兰人运回国内制作烘焙食品。

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第一次宴会的菜单上,也记载了使用香橼制作的面包,我猜这种面包,类似今天意大利人在圣诞节期间制作的潘娜托尼面包(panettone),配料表里必须有糖渍香橼。类似做法的更早记录,来自公元前6世纪的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犹记得多年前,我在瑞士为一位意大利裔泥瓦匠拍摄肖像,对方与我分享的一个生活上的秘密,便是圣诞期间要开车回意大利老家购买正宗的潘娜托尼面包。
迪亚蒙特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濒临第勒尼安海。这里从10世纪开始,就以出产迪亚蒙特香橼著称。这种果皮光滑的香橼只种植在Tortora和Belvedere Marittimo之间40公里长的区域内,这片区域也因此被称为香橼海岸(Riviera dei Cedri)。对于犹太人中信奉犹太教正统派哈西德教派的卢巴维奇派(Lubavitcher)而言,迪亚蒙特香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相信,摩西派了一个使者来到迪亚蒙特,收集当地的香橼样品,向犹太人展示他们在庆祝住棚节时应该使用的圣果。这个节日是犹太人的秋季感恩节,为了庆祝丰收和他们的祖先在沙漠中漂泊了40年而幸存下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