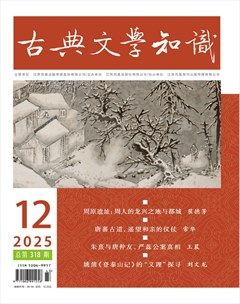1933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称《文学史》)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义基础上出版。这部20世纪30年代唯一以“现代”命名的文学史,篇幅达三十万言,但论白话文学部分仅万余字,且将叙述终点定格于新文化运动前夕,并侧重选录江浙文人群体。因其看似“守旧”且“名不副实”(如马玉铭《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二)》),在思想激荡的30年代引发诸多“偏狭”与“守成”(如穆士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一)》)的批评。然而,若超越“现代性”话语,回归民国知识分子语境,则可洞见其在时代剧变下折射的江南文人文化自救意识—通过文学史编纂重构行将消散的文人共同体。
《文学史》编纂的江南文化基因
钱基博《文学史》的地域特色根植于深厚的江南文化基因,此基因经由家族传承、书院教育和江南士人影响共同建构,在潜移默化中启蒙着钱氏的学术思想。
无锡钱氏家族自明清以来形成的“经史并重,文行合一”(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家学传统,为钱基博文学史编纂提供了文化价值根基。堠山钱家累代教书,自五代吴越王钱镠而下便恪守《钱氏家训》“读经传则根柢深”“教子读书是第一义”的教诲,《锡山钱氏丹桂堂支谱》卷首《族规》亦有“子孙毋废经史,尤当以《通鉴纲目》考历代治乱”(《锡山钱氏丹桂堂支谱》)的训示。钱氏自幼便接受严格的经史教育,他“九岁毕《四书》《周易》……《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大家选”(曹毓英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自传》)。这种经世致用的教育导向一定程度上为钱基博共同体理想的形成提供学术基础,并在《文学史》的编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在开篇绪论部分便总述其“根于民性”(《文学史》)的经世文学史观,分析梁启超政论文如何以文学为工具唤醒国民意识,肯定曾国藩等人调和“义理”与“经济”,评价严译《天演论》有“欲以文辞载道,拯溺济危……其救世苦心可见矣”(《文学史》)等。
钱基博早年就读于南菁书院,其“汉宋兼采,经世致用”(丁福保《畴隐居士自传》:“忆甲午年课题‘论管子盐铁政策与今日两淮盐务’,山长批云:‘能以经术断时事,此真南菁学风。’”)的学风与书院课艺批点中常见的“以史证经”的方法,塑造其文学史编纂独特的评点范式,在《文学史》中则表现为对章太炎“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的评价。
书院教育中的规训制度影响着钱基博文学史编纂机制的生成。南菁每日辰时经史辩论训练,使《文学史》叙事呈现强烈的对话性,常见“某曰”“某驳曰”的论辩体例,实为书院“会讲”制度的文本转型。书中大量征引历史事件(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作为文学背景,体现书院“以史带证”的教学实践。院长黄以周“文不空言,言必求效”(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的训诫,则直接表现为钱氏对张謇实业文牍等“实用文体”的特别关注,与同期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纯文学取向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然,南菁书院特有的“吴学底色”亦使钱基博的编纂实践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重视考据,批评桐城派圭臬方苞“好以己意裁断,而小学未精……此其弊在轻考据而重义理”(《文学史》);另一方面又主张“义理为体,考据为用”,如评章太炎《国故论衡》“虽极考据之能事,然其根柢在义理”(《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