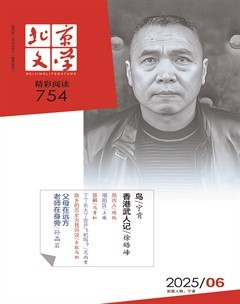小说以“我”的视角,窥见当代校园知识分子的堕落与溃败。中年教授面对贪腐的老教授,最终将其举报。小说冷峻的叙述中传达出对社会担忧的热道心肠。
*
正是上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又从北京回到这个中部城市的家中。一天早上,父亲正开车去火车站打算去参加同学聚会,结果半途又折了回来。他面色凝重地在家翻找了一些陈年材料和证件,便出门去了,直到晚上才回家,不同寻常地多喝了几杯白酒。
“我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呢。当然了,我是规规矩矩的。”
“到底怎么啦?”
“何教授出事啦,巡视组发现了他的事情,这几个月一直被关在小房间里呢。他们早上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只好退了票。谈了一整天,就是为了了解何教授的情况。……总之,人不能沾上一点污点,像何教授这样,一切都完啦,听说他儿子学费都没有了。”
“那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现的呢?”
“秦教授举报了他。我刚刚打听了一下,反正别人是这么说的。”
这几个名字并不遥远。何教授的儿子何嘉耀曾是我幼年最好的玩伴之一。
吃完饭洗碗时,一些久远的印象和画面在我脑子里复苏起来:在我小学低年级之前,常常是晚饭后,父亲会坐在狭小的桌子边上,用工整的字体,把军事史课件的要点抄在幻灯片上,有时配上必要的地图。那是人们还没有使用电脑的年代,这样的工作方式很原始,也很让人觉得安心。像这样誊抄着文字制作课件的人,构成了那时我所生活的社区的主要部分。我长期没有想过,这样稳固与和谐的表面会隐去甚至压抑怎样的波动和裂纹。
秦老师就是这样的一种裂纹。到了周末,这名化学教员会一个人出门逛逛,在商场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不像其他人那样总是为了买点什么。他似乎什么也不买,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更大一些了,正在上初中。父亲告诉我,这个人离婚了,而且没有孩子。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十分常见的事。它的潜台词是这个人毕竟总有些毛病,而且生活得十分孤独,可以说是凄凉。我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就不假思索地对他同情起来。
*
尽管洪云已经不再在这个单位工作,但仍然时常去秦老师的办公室看看,感觉那些不起眼的名片盒、钢笔、报纸和茶杯勾勒出的线条的韵律,在它们折射的带着潮气的光线中待一会儿。很多年来,他是一个象征,以沉默的方式解释了她对于自己生活倍感困惑的那些部分。
何教授——也就是洪云的前夫也曾坐过这个位置。每个清晨,阳光从无数面相同的阔大窗户照射进来,操场上响起亘古不变的早操音乐,同一拨老年人开始锻炼身体,几个打扮精致的幼儿园老师正出门遛狗,人们纷纷骑车去往工位,碰到熟人在路上恰如其分地减速停车致意。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幸福,最多是有些被前程激起的躁动不安。洪云不禁会猜想:他们真的都如此幸福吗?
和其他人不同,秦老师办公桌的玻璃桌板下没有任何私人照片或家庭合照,显得干净而空荡。洪云每次仅仅是想到秦老师的存在,想想他还在那里,就知道在虚空中的某个地方,保存着某些不被人注意的迹象和细节,散发着来自过去为数不多的美好时光的复杂色泽。这样的日子,裹挟着洪云青春时代或九十年代本身的喧哗和骚动,虽然刚刚从她身上滑落不久,却已经成了那些固定在玻璃匣子里的干燥的蝴蝶标本,逼真、鲜活而又脆弱、喑哑,无法发出一点点声音。她并不知道最近几个月来秦老师身体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把他微弱的烛光一点点捻暗,让他一点点地不在那里,一点点地从这个整洁的工位上流失。
*
让幼年的我对文学志业抱有一丝兴趣的启蒙者之一,就是洪阿姨,也是我的玩伴何嘉耀的母亲。洪云原本在中学教英文,喜欢读书。因为常常和何嘉耀一起放学,她和我见得很多,还偶尔指导我读点外国名著。不过嘉耀出生后不久,她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在那个人们纷纷出门做生意赚钱的年代也做起了跨洋生意。当时单位里即便是文职人员也都还都穿军装,工作日的时候,周围很少见到人穿其他衣服。但洪阿姨总是会穿艳丽的裙子,有的还很短。在我看来,她就是我未来想成为的样子。
我上大学后,和洪老师渐渐很少碰到了,即使偶尔碰到,也觉得她似乎变了个人。她变得愈发沉默寡言。在路上见到,她好像也已经想不起来我这个人了,更不要说和我谈谈什么。
到了大二,正值假期,我回老家待几天。一个平常的秋日,我出门散步,走在雨水和几片圆润的绿色落叶之间,这时碰见了远远走来的洪老师。附近的学员们正在练习射击,尽管没有实弹,但众多上膛的声响在某个刹那紧密叠合,仿佛在鸦雀无声的音乐厅里,钢琴键忽然发出的单独音响。就在这个细小声响变得脆利、明晰因而更显寂静的下午,洪老师从水汽中浮现,她目光明亮,也许突然又记起了我,径直朝我走来。
我近距离看了看她的脸,还保留着十多年前的样子,只是添加了一些起伏不平的皱褶。您最近还好吗?面对我的寒暄,她只是说,嘉耀很好,他在美国读书;她还说,你还在读文学,写东西,这比什么都重要。
归根结底,在青春期,文学给了我一种想象性的正直和庇护,因为我固执地以为,劣等心灵无法在这个领域骗取真正的荣誉,这种荣誉不是被金钱和销量衡量,而是被绝对价值所衡量的。当然,我后来明白,这是种过于理想化的期待。然而对于以做题度日、没有多少娱乐的中学生来说,这一点点自由的快乐已经足够了。至于为什么要把文学和某种道德上的纯洁明亮联系在一起,诸种原因暧昧模糊,彼此重叠,几乎无从描画,或许和我始终觉得难以获得真正的友谊有关。
从小学到中学,我内心确认的唯二的朋友,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茗子和嘉耀。另外还有班里两三个女生,也许可以算作并不交心的玩伴。茗子是差生,但她率真,直接,热爱音乐和漫画,相处起来让人放松。我和她的牢固友谊向来是被老师们反对的,这更使我觉得维持这种友谊无比正确。
何嘉耀是我们这个松散的女生小团体里仅有的男生,脾气很好,有些轻微口吃,和很多女生都玩得来。嘉耀时常约我们去他家里玩,多半在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他有个总是很忙碌的电气工程教授父亲和经常出差的母亲。我们都喜欢去他家做客,用来逃避自己的家——我们的家只意味着没完没了的做作业和极为有限的看电视时间。更何况他家很大,至少对那个年代的平均水准来说,一共有四个房间和很大的客厅,采用米色番龙眼地板,地面被擦得锃亮,电器和家具都很新。
洪阿姨有时出国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就会有一名叫小窦的“保姆”住在嘉耀家里。小窦原本是幼儿园里的舞蹈老师,现在不出门做事,只是靠何教授养着。她一天要为他们做饭一次,四菜一汤。似乎整个院子里只有嘉耀一个人相信这个故事。后来长大了一点,我们都猜想,那两三年里,小窦与何教授的关系,是洪阿姨所默许的。也许洪阿姨有其他更要紧的人生计划需要完成,也许她赚了许多钱但依然只是对这些无能为力,又或许她并没有什么职业,只是在国外游玩,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嘉耀从不仔细解释他母亲在做些什么。上中学后,洪阿姨就带着嘉耀彻底搬了出去。
不管怎样,在那两年,我们每次去他家都会照旧配合演出。在跟小窦阿姨打招呼的时候,不得不掩饰我们不知从何而来的嫌恶和悲哀。(这不是我们唯一需要配合演出的场合,比如在另一名女同学邀请我们去她家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要装作不知道她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似的,一边欣赏她母亲囤积在卧室里的等待转手的诸种货品,一边谈论她不在家的、在外地做领导的父亲。)我们都认识洪阿姨与何叔叔,从我们会认头几个汉字的时候就开始经常礼貌地称呼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