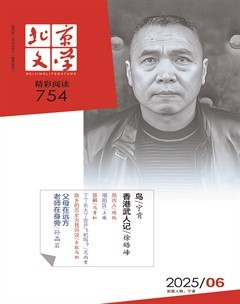月亮每天的位置总会有所变化,月亮会走,和人一样。农家老妪潘奶奶时常坐在门口的马扎上看月亮,月亮于她,既是时间流逝的见证,也是孤独生活的陪伴。我们借由她对月亮的凝视,看见了一位老人寂寞的内心世界。
月亮永远都在天上,却总是不会出现在前一天的位置。潘奶奶早就发现了,但她不像孩童发现某些自然规律时,表现出格外的兴奋,她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
月亮是会走的,和人一样。
潘奶奶从前在乡下,只记得夜晚很亮。麦田里、猪圈上,都蒙着一层月亮清清亮亮的光,那时候的人们很少会注意月亮,除非是八月十五前后;而今潘奶奶瑟缩在骨灰盒似的小屋里,屋外与门框的夹角视线固定,在夜晚,稳定占据着一小片的夜空。
潘奶奶喜欢坐在门口的马扎上看月亮,她看不清星星,尽管有时候星星也会出现。偶尔失神盯得久些了,潘奶奶吃惊地发现天上有芝麻大点的火光,幽幽闪闪的,像一个个烟烛头在反复烫开一件巨大的皂衣。她欣喜,却没人可以分享。
后来潘奶奶和别人分享了,人家告诉她,那是飞机——火红的光是飞机的夜航灯,所以一闪一闪的。宿迁旁边是徐州,是淮安,那边都有机场。
他奶奶的,原来是飞机,潘奶奶撇撇嘴说。
那人接着说,我在抖音里看到的。
潘奶奶问,那什么音里有没有说飞机会不会撞到月亮?它们都在天上,而且月亮不安分,跑来跑去的。你不知道,晓霞马上要带泽恩坐飞机去上海玩,我不放心。
不会的,潘婶,放心吧。
潘奶奶回屋洗漱的时候还在想这件事,她不相信什么音里说的,她也不相信卖猪肉家的二儿子,他是生意人,嘴里没有实话。所以,一辈子没有信仰的她依然要像前几夜那样,在黑暗中双手合十,替儿媳和小孙子祈福。
二十平方的门面房承担起一个古稀老人的起居绰绰有余,况且潘奶奶的生活很简单。房子外面有个遗留的旧招牌,暗淡失色的红底白字写着:邱记面馆。进门处有个小木桌,两个小木椅,潘奶奶吃饭的时候就在这张桌子上吃,桌子上面有一张发黄的塑料膜,膜上似乎是陈年老油,总会粘住碗筷,就算手拄在上面久了,拿下来也会发出噼啪的响声。
桌子旁是儿子郑毅家拆迁撂下的旧鞋柜,现在用来摆米面粮油和作料,偶尔也摆一箱牛奶,郑毅带来的。潘奶奶故意把牛奶放得高高的,有人来便指给他们看,像是讲解员介绍文物那般,骄傲地说:
这是俺儿子送过来的牛奶。
再往里就是床,是潘奶奶还在郑毅家住的时候睡的那张。农村土房拆迁以后,她似乎一直都睡在这张床上,人虽辗转,床却不变。床垫也是,老家伙了,像潘奶奶松弛的皮肤和肌肉一样,床垫子也失去了它原本的弹性,跟人似的,老了,没脾气了,谁欺负,就由他欺负吧,再没有年轻时的那股子劲儿了。潘奶奶坐在上面,床垫就顺服地趴下去,潘奶奶起来,床垫上仍有一块屁股蛋那么大的凹陷。非要等潘奶奶不去看它了,它才老态龙钟地悄然复位。小孙子郑泽恩来过几次,他喜欢在奶奶的老床上蹦,新奇,有种慢回弹的触感,没脾气的床垫像是死掉了。之后郑泽恩回家,两只脚都得了脚气,脚底和小腿上长满了透明的毒痘痘,一挤便有毒水射出来,在那之后,除去过年过节,小孙子再也没来过了。
床冲着大门,人在外面走,能看见潘奶奶的两只皲裂的脚底板。郑毅看见了,说,妈,太丑了。一语双关,像在替儿子郑泽恩的脚气鸣不平。郑毅决定在老娘的床尾处加一个屏风,于是他去当地的义乌商贸城转了一圈,纠结了一会儿,回家后把家里的破窗帘带过去了。郑毅在屋顶打洞,这是房东允许的,因为这里很快就要拆迁,要不了几年。破窗帘被悬挂在潘奶奶的床尾处,斜着耷拉下来,像一只垂头丧气的吊死鬼。潘奶奶不喜欢这个,她觉得半夜这个窗帘会盯着她看,要把她带走一样。潘奶奶对儿子说了,但她不能说吊死鬼,因为这么说她没面子,好像显得她很幼稚,于是她对郑毅说:
窗帘,挡住我看月亮了。
窗帘被拿下来之后,潘奶奶也看不见月亮,当然郑毅不知道老娘骗他,因为他不愿意睡在老娘的床上,自从郑泽恩脚上长满了脚气痘,哪怕他只是碰一下老床,也要跑到卫生间去洗手。有次他帮老娘晒被子,晒完了去屋里洗手,顺便撒尿的时候,他发现马桶被老娘用坏了。怪罪了几句,撂了一会儿脸子。
其实潘奶奶搬过来的第一天马桶就坏了,上一个租客弄坏的,邱记面馆的老板。潘奶奶没跟儿子说过,她觉得有些尴尬,到底尴尬什么,她说不准。她为了自己心底的那点腼腆,决心每日往西走三百米,过两条马路,去菜市场后面的公共厕所如厕。凉亭里打牌下棋的老头老太太总打趣她说,潘奶奶又去买菜喽。
儿子郑毅以为是她用坏了马桶,潘奶奶心里酸溜溜的,却也没有辩解。儿子虽然嘴上厉害,心是向着老娘的,他找人修好了马桶。修马桶的是个年轻人,他对郑毅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坚硬的屎,吸不上来,捅不下去,老太太真厉害。修好马桶正好是去年冬至吃饺子的时候,潘奶奶留郑毅吃饺子,跟小时候一样,芹菜猪肉馅的。郑毅说,不吃啦,晓霞和泽恩还等着呢。
虽然没留住郑毅吃饺子,但马桶修好了,她再也不用顶着寒风去公共厕所冻腚了,潘奶奶很高兴,而且她再听到打牌的老头老太太打趣她时,她也不用疾步躲开了,而是可以笑着回应:
是哩,我就是去买菜的嘞!
厕所在床里边,尿臊味就弥漫在床头,潘奶奶不在乎这个,人老了,嗅觉变淡了。听觉也是,二楼三楼住户的冲水声到了潘奶奶耳朵里,像是有人用勺子轻轻刮搔碗底一样,不痛不痒的。厕所旁除了一个发霉的小橱柜,还有一个荒废的洗手池,水龙头被霉菌蛀满了,糯米馒头似的肿胀着。白瓷水槽也被锈水蚀黄,留下水流样的瘢痕,黄色的瀑布一般挂着,通连到黑洞洞的下水道口。几只蛾蠓永远伏在洗手池附近的那几块瓷砖上,长在上面一样,从来不见挪窝。
潘奶奶是前年年底搬过来的,过年的时候儿子儿媳还把她接过去了。隔年,也就是去年,就没人接她了。为什么不接?她想过,也许是因为自己用不来智能马桶,弄得满地都是水;也许是给孙儿的红包不如他外公外婆的多;也可能是儿媳坚决不同意,两口子因为自己又动手动脚了。潘奶奶想到最后,总会开解自己,算了,不想了,不去也好,过年没什么大不了,初一小孙子还是会来磕头的,这就行了。邻里邻居也没人说闲话,因为他们也都各自去过年了,谁会留意她这户小门面房亮不亮着灯呢?
想到这些,潘奶奶有点心酸,老家2006年拆迁,儿子用拆迁款买了套安置房,她和老郑半辈子的心血被挖机碾碎成泥,满地都是岁月流逝遗留下来的痕迹,而后它们成了潘奶奶心口的疮疤,日日夜夜反复发炎刺痛着她衰弱老朽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