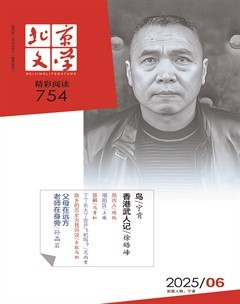“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藓如此,青春时代隐秘难测方生方死的情感也是如此。我和女孩木羽偶然相识,她向我索取真心与爱情,我给不了她,退无可退,掐断了联系,直到她再次出现……
山城很热,太阳直直地烤在身上,汗液很快蒸发,手臂灼痛,被一层盐渍覆盖。约好的顺风车走错了位置,我蹲在一棵小树的影子里,鞋底仍在持续熔化。
司机是本地人,典型的网约车型。电话一个接一个,车子左拐右拐左拐,在城里绕了一个多小时才上高速,抵达酒店的时候已经不早了。将背包扔在桌子上,我直接躺在床上,玩了半小时手机便睡着了。直到天黑我才醒,洗了把冷水脸出门。
空旷的灼热并未消失,酒店对面的小区门口传来广场舞的音乐,因为背光,舞动的身影只有轮廓。夜生活刚开始,烧烤摊上的吆喝不绝于耳。整条街道都被劣质烤串的气味笼罩。
选了一家有空调的烤串店坐下,扯了张纸巾擦掉额头上的汗水,我才开始点菜。这里的人似乎并不怕热,大都围坐在室外,兴许是早已厌倦了整个白天都困在空调房里,趁夜显得相对凉快时,透透气。
室内就我一个人,吃掉的半条鲫鱼和两串鸡郡肝缓解了饥饿。店内人少,老板娘上完菜后,坐在吧台前,问我是哪里人。
“要不,喝一杯?”我试探着地问道。
她端着一杯啤酒过来敬酒,剩下的大半瓶都留在了桌上,又拿来一瓶没开过的,算她请客。我感谢她的好意,但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喝啤酒,自费要了一瓶白酒。
“生意不好做。”她坐了下来,把自己的杯子倒满。
烧烤店的位置并不偏僻,但街道上的人和车都不多,亮着的路灯显得有些多余,刚从门口进来的顾客显得更多余。老板娘起身招呼客人,理了下包臀裙,手是贴着臀部曲线摸下去的。
我坐在空调旁边靠窗的位置,老板娘坐回了吧台。见我和老板娘聊着,刚来的女孩也搭起了话。感慨天气一年比一年热的时候,在老板娘的提议下,两人都坐了过来。
两个女性的酒量都不差,老板娘叫露姐,另一个叫木羽。木羽很开朗,符合她少数民族的身份,有一半的时间都是我们端着酒杯听她讲述。
结账离开后,我不知道去哪里,便接受了木羽的邀请。同露姐道别后,两个人沿着河堤散步,时间不算太晚,但白日的炎热已然消散不少,不时有风拂动头顶的柳条。我贴着大理石栏杆伸开双臂吼了一声,声音消失在宽阔的河面,没有一点回响。
风一吹,酒劲上来,我邀请木羽到我的房间喝茶醒酒,酒没醒,我醒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晨。被子和衣服都落在地毯上,木羽的手搭在我的胸口。两分钟后,她也睁开了眼。没有说话。
吃过早餐,我表示要单独走走。从酒店退房出来,我背着行李上了一辆出租车。上午的风已经开始热起来,吹落汗珠的同时,也将我的心思吹落在长江里。一直想看的长江,不过是河床更宽流量更大的涪江。其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水是从涪江来的,从涪江上层层拦截的电站、水库溢出的,我也是。都是流失的部分,未被拦截的部分。下游还有更多更大的水坝,但站在这里,我似乎就能看见大海,看见开阔,看见水更接近自然的状态。
我从涪江上来,走了二十年,终于走到了长江。和我一样从涪江来的人,有许多已经走得更远,抵达地图上看来零零星星的岛屿,但仍有许多尚未抵达长江,还困在涪江的某一条小支流甚至连支流都算不上的无名小溪。
回到涪江,已经傍晚,气温比山城低一些,但仍不时冒汗。在成都转车时,收到木羽消息,约晚餐,她说与烤串店老板相谈甚欢,我祝他们聊天愉快。
打开出租屋的风扇,迎面而来的仍是热浪。我决定到芙蓉溪里游泳,这是住处离涪江最近的一条支流。
时间附着在浅滩的石头上,整条河在某种情绪的支配下,开始茂盛,也开始衰老。
路过一处深水区的时候,河堤上围了一大堆人,我靠近了些。人群中间,一个头发散乱的女子,和一个紧拽着女子衣角的年轻男子。女子半个屁股搭在栏杆上,半个身子探向了悬崖,只剩一只鞋子还挂在脚上,另一只鞋子提在男子手中。通过围在旁边几个老太的劝解,大概得知二人是情侣,吵架后,女子便萌生跳河的念头。
见已有几个年轻人上前劝阻,我便上前,朝着上游浅滩走去。一来既是当着众人面做此状,那便并非真正想要轻生。二是已有足够的人阻止这一事件演化成悲剧,已不需我多做什么。
果然,我还没拐过弯,就听见身后一阵呼声,小情侣搀着离开后,众人也纷纷散去。
脱衣服准备下水时,木羽发来一张和烤串店老板的合照。我把刚脱一半的裤子穿上,坐在石头上,把刚才发生的一幕简要说了一遍,也发去了一张芙蓉溪的照片,照片拍到了我脱下的衣服。
他们都对我未能到场感到遗憾,我表示祝福后,便放下手机蹚进河流。浅滩满是石头,爬满了青春短浅而柔密的胡须——苔藓。
由于过于投入地感受脚底传来的冰凉滑腻的触感,我摔了一跤。那一刻,整个河面向我迎面撞来。我整个人被掀翻在水里,顺着水流滑了三米开外才停下来。脚踝的疼痛让我想要立刻跳起来,但理智告诉我,必须避免再次跌倒。
疼痛稍缓,我再次注视这条河流。
它一直在等待游泳者,等得满身灰尘。但有人靠近时,它又总是以痛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