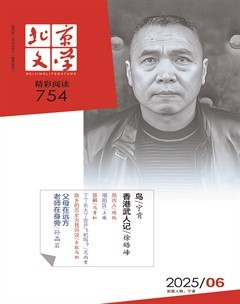局群被命名为“我爱我局”,机关所有人都在群里,宛如一个大家庭。从工作思路到职工生日,众说纷纭建言献策,每天“我爱我局”里都如赶大集般热闹。张一元在群里表现不太积极,显得很各色,这事儿可把他给愁坏了……
床离客厅——确切地说,床离手机的距离(手机搁在客厅茶几上)足有七八米远,而且卧室门还虚掩着,手机又设置成振动——尽管如此,张一元还是敏锐地听到了,或者说察觉到了:刚刚有一条微信。
这天是周六,张一元在单位加了一天班,九点钟回到家。妻子李沐湘对他周末加班颇有微词,认为他是故意找碴冷落她。春天来了,憋了一个冬天,疫情防控也不那么严了,他真该陪老婆出去转转,到郊外踏青也好,逛逛商场也好,找个地方喝喝茶打打牌也好——可他每个周六都要加班!
周日上午照例要睡懒觉,中午一般要到张一元父母那边转转,他陪他父亲小酌两杯;下午再转到她父母那儿,简单吃个晚饭,回到自己小家,已经很疲惫了。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又要爬起来上班,做什么的心情都没有了,简单洗洗就背靠背睡了。
周一到周五呢,更不用说,名义上都忙。白天诸事缠身,晚上要么加班,要么应酬,回到家,常常是累得话都懒得说。尤其张一元手不离手机,像患上手机综合征那样,蹲厕所、洗澡,都要带进卫生间,夜间也不关机,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来条微信都要一个激灵,像接到命令似的,说不上是激动还是恐惧;每天盯老婆的时候少,盯手机的时候多。
看手机真有那么重要吗?
张一元反复解释过。
李沐湘不全信。一时怀疑他外面有人,可又没啥证据。
结婚一年多,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在李沐湘眼里,张一元越来越让她感觉陌生;而在张一元眼里,她是不是也这样了呢?
但是这个周六,晚九点,张一元回到家,突然感觉气氛有点朦胧,有点异样,有点怪怪的。李沐湘已经沐过浴,发型是新换的,平添了喜兴和洋气;着一套张一元以前不曾见过的鲜艳的睡衣睡裙,似乎有意地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偶尔抛来个媚眼;身上还洒了香水,而她以前晚上是不用香水的,说是浪费。张一元不觉有点儿脸热心跳,忽然想到作为丈夫应尽的责任。
二人都已年过三十,双方父母早就有意无意提醒过生娃的事……是的,这事总不能无限期拖下去。
张一元心知肚明,立即做出回应——进卫生间洗漱冲澡,破天荒没把手机带进去。出来时,李沐湘已经进了卧室,大灯关着,开了床头台灯,光线朦胧、神秘、美妙——以前怎么没发现床头灯这么有情调呢?因为很少开,常常是她睡着了,他才摸黑钻进去。
是否把手机带进卧室?上床之前张一元稍稍犹豫了一下,最后牙一咬,心一横,调到振动上,决绝地往客厅茶几上一搁,有点迫不及待地进卧室,扑上床。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动人!从前戏开始,二人极其地投入,少见地和谐,罕有地畅快,李沐湘都叫出了声。而在以前,他们大都像公事公办,似乎以应付为主,享受为辅,浮皮潦草,早早结束为盼。但是这个晚上,真不一样。张一元忘记了一切的烦忧,纵横自如,李沐湘眼看就要被他征服……
幸福持续了好久好久,感觉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高潮即将到来。然而,实在不巧,就在那个瞬间,嗡的一下,像有一只蚊子飞过耳际——张一元确凿无疑地听到手机发出了一点振动。
没错,是一条微信。
此刻,正待最后冲刺的张一元,仿佛接到一个紧急命令,忽然间停了下来!是的,他停了下来,拿不准是不是泄了,反正软了。李沐湘骤然之间也随之降温。她恼怒地睁开眼,狠狠剜他一眼,满脸羞愤,随之扭过脸去。
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是没发生过;只不过今天的反差太大,令李沐湘难以接受。
张一元脑袋里想的却是:都十点了,谁还发微信?
一定有要紧事!
张一元不再磨蹭,从李沐湘身上一跃而起,光着身子,赤着脚,快步奔向客厅,摸过手机一看,果然是一条重要微信——处长李涛发来的:一元,赶快看一下局群,王局有指示。
他当即回复:收到!好的!
全身赤裸的他感觉有点冷,也顾不上穿衣服,蜷缩进沙发,点开局群,快速浏览起来——
大约半个小时前,“永不止步”在“我爱我局”发出一条重要微信,大意是,下周要进行年度工作总结,并布置明年工作,希望全局人员结合各自或本单位工作实际,认真思考一下,今年有哪些主要成就?明年有哪些打算?对局里有哪些意见建议?请各位同志尽快发到群里,并请局办注意收集,下周一上班后归拢。
“永不止步”就是本局老大王局。指示发出后,满打满算,才半个小时,六十五人的局群,就有三十多人起而呼应,踊跃发言,感觉都在争先恐后,兴奋异常,群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有些人的发言,一看就是提前精心准备过的,不像是临时跟帖。这部分人似乎号准了王局的脉,早料到王局会有这一手,所以都胸有成竹,第一时间拿出了有质量的跟帖发言。王局当然不会冷落大家,频频点赞、互动。这更加地鼓舞了众人。局群热闹非凡,让人都觉得手机烫手。
这样的场面早已是常态。不光白天,经常是临近半夜,“我爱我局”像烧红的烙铁,突然热起来。从中亦可窥见本局同志的敬业精神。
张一元粗略数了数,他所在的三处,除了他,其他九人由处长、副处长带头,或长或短,都做了“粗略”的、“不成熟”的发言。显然跟李涛处长的及时督促有关。李处经常谆谆告诫全处人员,你在群里说什么并不重要,局领导也不一定认真看,只要你参与就行;既然要参与,那就赶早不赶晚。还说,你不冒头、不理睬、不吭气、反应慢,尤其老是潜水装死,那是万万不可的!
张一元不想落后,理理思路,皱起眉头想了一段话,打出来,看看没有错别字,没有明显的不妥之处,屏住气息,手指轻轻一点,发了出去。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只听卧室里发出一声闷响——如果没猜错的话,李沐湘把他的枕头扔到了地板上。
一年前,王局来本局上任。俗话说,换帅如换刀,年富力强、思想开放、大刀阔斧、敢于担当的王局很快为本局带来崭新气象。
人们没料到,王局上任后点燃的第一把火,竟然是建群。谁都承认,微信的出现,为交流带来极大便利,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距离,也为工作插上了信息化翅膀,提高了办事效率。可是,以前的老局长压根不感兴趣,信奉四平八稳老一套;从局到处,虽然也都建了群,但是老局长端着个架子,就是不入群。有什么事,或者打电话,或者到他办公室汇报,你想加他微信,门儿都没有。这样一来,几个群都成了摆设,半死不活,可有可无,偶尔局办在里面发个无关痛痒的通知,也没人当回事。
王局一到任,立马不一样。他提出,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好现代化的办公手段?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你不用网,一定会被社会淘汰,成为一个边缘人。在王局的指导下,新创办了公众号,局群被命名为“我爱我局”,以全新的面貌高调创立;局机关所有干部,从局长到科员,一个不能少,全都拉进来,而且为便于监督,必须实名。三位局领导情况有点特殊,自然无须实名,王局是“永不止步”,赵副局是“山高人为峰”,孙副局是“春华秋实”,都很好记,颇有正能量。当然,这也凸显了上下有别。另外还设立了处室以上领导参加的党组群,那是个小圈子,所聊内容,外人不知。
在此背景下,局办和五个处也都雷厉风行,高调行事,大张旗鼓建群用群。三处的处群,命名为“和谐三处”。李涛效仿局领导,不用实名,在里面他是“涛声依旧”;别人呢,对不起,当然都得实名。
后来还根据每个阶段的工作情况,临时设立各种不同的工作群、专班群等等。一时间建群成风,一天不拉几个群手就痒痒,仿佛这一天白过。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爱我局”,局机关所有人都在一个群里,仿佛一个大家庭,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口大锅里捞饭吃,其乐融融,想想多么暖心呀!以前的老局长,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都以为这股风很快会过去——我们手机里面大量的群,也就刚建群那会儿闹腾闹腾,眨眼就没了人气,成为僵尸群,是不是?
这回,人们想错了。
“我爱我局”从建立那天起,每天都像赶大集那般,热闹得很,就不曾消停过。
说到底,一切都归功于王局。
王局这个人,与其他领导不同。他为人热情,思维活跃,做事干练,从不拖泥带水,尤其能够降低身段与部下打成一片,他真的没一点架子。不说别的,只说在群里,他比一般人还活跃,甚至可以说,他是最活跃的。感觉他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像蜜蜂采花那般辛勤,又像蜂王坐镇蜂箱那般稳若泰山,有他镇守,人们趋之若鹜也便理所当然了。
对于本局工作,不论大小,凡是能够往外说的,一律在局对外公众号上发布;王局带头转朋友圈,并要求所有人第一时间转发。你转了,他就点赞表扬;你不转,他虽然没说啥,但心里面恐怕是不乐意的。
至于“我爱我局”,只要想说,不愁没话。从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市里的大事,到本局的各项工作、局领导的工作思路和想法,以及各处的工作安排等,只要有人抛出来,就够阐释、解读半天的。此外,还有群众建言献策、哪位过生日、谁家生了二胎三胎、谁家孩子考上了重点、谁谁升职了、老同志退休、新人入职、节日祝福,等等等等,说不完的话,扯不完的事,让你总感觉眼睛不够使。
没过多久,“我爱我局”就产生了溢出效应——本市日报有位记者写了篇报道,说这个群虽小,但它拓展了空间,温暖了同志,增进了友谊,凝聚了人心,加强了团结;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办事效率,弘扬了正能量,密切了干群关系。是一个展现本局精神风貌的最佳窗口,像一面镜子,从中照见局领导与时俱进的工作思路、扎实有效的工作作风和开拓意识。据说市长还在市政府办公会上提到这事,号召其他局借鉴学习。
关于这个话题,群里简直像过大年一样,足足谈论了三天。
张一元一开始就没跟上形势。他性格有点散漫,有点不上心,遇事不急不躁,不知轻重;顶着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总给人感觉有点孤傲,有点摸不透。对于整天捧着手机看朋友圈,还要不断在群里跟帖发言点赞表态说好话做总结谈看法,他很不习惯,很不习惯。一句话,他不大积极,甚至有点抵触。
李涛处长每天都盯着朋友圈,重点监督本局公号文章你及时转发没有?你在局群露头没有?都说了啥?和其他处室相比,本处同志的参与度高还是低?热还是冷?王局为谁点赞多?……林林总总,这些都得让李涛操心。这个处长,不好干。
他最不放心张一元,两天不见,就转到他办公室来,委婉提醒道,一元啊,不能搞特殊嘛,更不能骄傲自大噢!没话说,点个赞,献个花,发个笑脸,总可以吧?有那么难吗?
张一元立刻意识到不好,马上赔个笑脸说,好好,处长请放心,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确实注意了一些,但还是达不到李涛的要求。
和张一元一个办公室的老周,则完全是另一副心态。老周好脾气,见谁都笑呵呵,像一尊弥勒佛。对于网上参与本局工作,他特别热情,天天捧着手机,兴奋得很,专找朋友圈里同事转发的本局公号文章,点赞留言举大拇指,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老网红。局群一有动静,他恨不能第一个冲进去。
有一天老周对张一元剖析心路历程,说,小张呀,你不知道,我们小科员以前想接触局领导,难着呢!现在呢,有了微信,有了朋友圈,入了群,加了好友,领导离你一下子近了,好比天上掉馅饼,多好的事!
老周每天一睁眼,就给王局、赵副局、孙副局、李处、徐副处,还有其他几个处的处长发私信,连图带文,什么早晨好、早安、早安快乐、早安吉祥、周末快乐、事事顺心、健康平安、幸福常在、吉庆有余、好运相随什么的,反正网上有用不完的表情包、图文包。至于逢年过节,那更是挖空心思抄袭或者自己改编,搞几句好词,第一时间为人送上节日祝福。
老周挤眉弄眼地对张一元说,这又不花钱,不送白不送。你送得多了,人家自会对你有个好印象。对不对?人心都是热乎的,谁不喜欢听好话?
张一元有些不解,问道,周老师,你老是发这个,人家会不会烦?
老周嘿嘿一笑,摇头道,有一次,王局见了我笑,笑得还挺开心。你说他像是烦我吗?
二处处长生了个二胎,大伙都在局群里面送上滚烫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话说得让人感到肉麻之余,又为同事之间的深情厚谊所打动。
李涛仔细数了数,本局绝大多数同事都发了言,三处唯独张一元忘了祝贺,他压根儿没露头。
这可不是小事。谁都知道,二处处长是王局红人,二处又是管人事的,绝对的核心部门,你张一元这么干,不仅是你个人的事,而且事关整个三处的对外形象。为了稍稍弥补一下,晚上,李涛特意给张一元发私信提个醒,没回;打电话,关机。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代表全处又给二处处长发了一条私信,再次送上热忱的祝福。
第二天一上班,李涛把张一元叫到办公室。李涛本来是个好脾气,轻易不发火,这一回没忍住,板起脸子道,张一元,昨晚给你发微信,为啥不回复?
张一元抱歉地一笑说,处长,对不起,昨晚大学同学聚会,喝得有点多,赶上手机没电自动关机,回家就睡了,没顾上看。
李涛哼哼道,你为啥不在局群里面给人家二处处长贺个喜呢?显出你牛逼、高傲?
张一元这才明白李涛的意思,赶紧说,哎呀处长对不起,昨天下午忙着赶一份材料,没怎么看手机……
无论他怎么解释,李涛就是不想放过他,最后甩下一句,说,为了与兄弟处之间搞好关系,这种事还是不要忘了,否则别人认为你有意呢。更不要忘了,你是三处的人,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是我们三处!
就为这事,李涛有好几天没怎么搭理张一元。
张一元这才意识到自己确有不妥。夜里,他失眠了。第二天去父母那儿,他把这事讲给父亲听。老头在区政府机关干了一辈子小公务员,退休之前连个正处都没混上。老头要求不高,希望儿子这辈子能混个正处,超过自己就可以了。
听了儿子讲的,老头戳了一下眉头,说,你是不开眼哪!你们那个群,可不是一般的群,而是一个江湖!局长、处长都盯着呢!为啥别人都抢着冒头,就你缩头?叫我说,你这个博士,若论情商,你连个高中生都不如!
张一元让父亲说得后背直冒汗。
父亲叹口气,又道,当年呀,我和你一样,假清高,不太上心这种事,见了领导绕着走。结果呢,学历比我低、能力不如我的同事刘全刚,人家不像我,最后混到了副局!多年来我一直不太服气,后来想通了,姓刘的就是比我会来事儿,自己没上去,不怪别人,就怪自己……
父亲唠叨起来没个完。以前张一元不爱听,这回他听进去了。
在群里发个言,点个赞;在朋友圈及时转发本局公号文章,这么点事儿,它有什么难的呢?只要你识字,外加手指头勤快一点,闭着眼睛都能办。
从这天起,张一元每天都告诫自己,这事万万不可再马虎,不然李处真要看扁你啦!他痛定思痛,决心洗心革面,端正态度,把这块短板补上。
几天之后,久不露头的“春华秋实”在局群向大家道别,说要到市委党校进修一年,暂时脱离本职工作,衷心感谢王局和全局同志对他的关心帮助。再见!
这位孙副局比较年轻,资历尚浅,平时相当低调。在局群里面,他是最不活跃的,长期潜水,不置一词。当然,因为他是局领导,没人敢说他。
看到孙副局的告别留言,勾起张一元对往事的回忆。孙副局不分管三处,平时和三处的人接触不多。张一元刚入职那年,局里组织下区县工作专班,他跟孙副局一个组,密切接触过几天,感觉孙副局这人朴实无华,不尚空谈,作风扎实,关心部属,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
张一元静下心来,结合自己感受,写了很长一段话,谈了自己对孙副局的看法,有细节,有情感,有温度,不吝溢美之词,并向孙副局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这是张一元入局群以来,第一次做出系统性、针对性的发言。而在他之前,仅有两三个简短的跟帖。这回算是抢了头筹,破天荒,难得!为此,他不由得有点沾沾自喜。
找个理由转悠到处长办公室,满心希望李处能夸他两句。哪知李处面无表情,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点开局群,看到跟帖者依然不多,不过十多个人,而且都是非常简短的客套话,有的仅仅发个表情包而已。就张一元那一大段话悬在那儿,像一团乌云。今天如此冷清,确实有点异样。往常可不是这样,屁大点事往群里一抛,人们都会蜂拥而至,大呼小叫,好不热闹。
张一元心神不定地回到办公室。老周笑眯眯地望他一眼,欲言又止。
张一元忍不住问道,周老师,今天局群这么安静,您知道为啥吗?
老周慢悠悠喝口热茶,想说什么,往门外看一眼,改口道,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
张一元更纳闷了,摇摇头,不知该说啥。
老周又往门口瞅一眼,压低声音说,孙副局这一走,恐怕很难回头了。
为啥?
老周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一口,又一口,吐出一团团烟雾,半天才道,为啥?这得问问王局。
老周讳莫如深地一笑,低下头办公,不再理会张一元。
其实这个时候,张一元已经顿悟到了,无须老周再点拨。意识到自己又办砸了,他颓然地坐进椅子里,半天没动,像一只落魄的犬。
张一元的朋友圈好友不算多,五百来人。近来,他总是积极给别人点赞,不管对方发出的是啥内容,看到就点。渐渐发现,自己毫不吝啬为人点赞,而为他点赞的却不多,也就是说“付出”多,“回馈”少;他还发现,那些不为他点赞的人,却乐此不疲地为另外一些人点赞留言献花送表情包——这另外一些人,都是地位相对高的。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点赞专挑比自己强的,这是一个有趣的规律,看来朋友圈也是论级别地位的。张一元一个小科员,收获的点赞主要来自本局的下属部门——各区局、县局的正科以下低级别公务员,一些没怎么混好的社会边缘人物,以及几个瞧得起他的亲戚朋友。就连老婆李沐湘,都很少为他点赞,视他为无物。
李涛处长冷落了张一元几天,后来看到他在朋友圈和局群开始变得活泛起来,或许觉得他“孺子可教”,重新对他展露笑脸,说,一元啊,一处的崔爱明,你熟悉不?
张一元说,比较熟悉,我和小崔是大学校友,我算是师兄。平时联系虽然不多,但话还是能说上的。
李涛笑笑,说,你呀,抽空跟他多聊聊,以后就知道怎么做了。
张一元早就发现,小崔在朋友圈几乎每天都在刷屏,搞得风生水起,涟漪阵阵。他会跟形势,会抓时机,会揣摩上级意图,会表达,所发内容大都与本系统本行业的工作有关,上承国家部委,下接基层区县,满满的正能量。就连王局都经常为他点赞留言举大拇指。这种待遇,处长们都没有。
在局群里面,小崔更是异常活跃。一大早,他第一个现身,日复一日不厌其烦为局领导和全局同事道早安。不管什么话题,只要有人抛出来,他总是积极响应,用心写帖跟帖,说的话让人阅着舒心,读着惬意。尤其是每逢王局在群里做指示、发号令、提要求,你看吧,十有八九是他最先做出回应;重要的是,他的跟帖都非常有质量,有水准,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高度有温度有力度,显示出很高的能力素养和文字水平。在众人眼里,小崔简直就像是为王局量身定做的回声筒。他在群里面的跟帖发言,完全可以搜集整理一下,印一本小册子供大家参考学习。
有传言说,小崔年底可优先解决正科。小崔学历仅是本科,其貌也不扬,但和张一元这样的博士相比,人家一点都不显弱啊!
前几天王局在群里发了一次火,因为他发现,自己每次在局群发个言,说点事;或者本局取得一点成绩,收获任何一项荣誉,只要在群里一发布,各处室都像比拼似的,变着法儿说一大堆奉承领导的话。王局本人很提倡实事求是,不喜欢光听漂亮话,所以就发了一回火,当然是那种比较温和的发火。王局明确表示,以后任何人不得再在群里刻意奉承、表扬、夸奖局领导,尤其不得再用“高屋建瓴”“重要指示”这一类的词句;要把功劳记在大伙身上,因为工作是大家做的。
王局一发火,“我爱我局”像被人浇了一瓢冷水,众人一下子变沉默了。像一个喜欢跑步的人,崴了脚脖子,不会走路了。局群少见地冷清了好几天,人们仿佛没了方向感。不让夸领导,难道都去夸群众吗?夸群众,能起啥作用?
都迷茫了。
这天上午,局办在群里发了一则通告:本局主抓的一个项目胜利完工,受到市政府通报表彰。要在以往,人们一定会欢欣鼓舞,纷纷跟帖赞扬局党委尤其是王局的重要决策和重大贡献,这是惯例。但是这一次,因为王局发火在先,大伙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少数人简短地说两句套话表示个祝贺,多数人只发个表情包应付了事,没有了过往精彩纷呈、你追我赶的长篇大论。
令人感到愕然的是,崔爱明依然故我,文风一点没变,像先前那样,借题发挥,借力发力,又把局领导给委婉地夸奖了一番,当然他没使用王局“反感”的词语。
有些人在等着看热闹——王局刚刚说过,你小子这不是“顶风作案”吗?
今天的局群,有点像不久前孙副局告别那天的场面一样——只不过上次是张一元出糗,今天轮到小崔了。
张一元不禁为小崔捏了一把汗。
中午在机关食堂,张一元端着盘子找小崔,看到小崔躲在一个角落里,便越过一排排桌椅走到小崔身边坐下。小崔一边吃饭一边划拉手机,注意力都在手机上,对张一元的到来并没有什么反应。张一元轻咳一下,开口道,师弟,我们李处让我来找你取经,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是怎样成为咱们局网红的?
小崔愣了愣,一时没作声。张一元态度很诚恳,不像是调侃。小崔也知道张一元是个认真型的书呆子,不会揶揄人。张一元小口嚼饭,耐心等待小崔开口。
小崔眼睛仍然不离手机,苦笑一下,说,师兄,只要把这事当成正经事来做,不要嫌麻烦,不要抵触它,心态要跟上,就成了一半。我上班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在群里看和写;业余时间不看电影不看电视,蹲厕所都不放手;儿子一岁了,我陪他的时间,寥寥。师兄,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张一元感慨地点点头。
做这个也上瘾,一旦上瘾,就放不下。小崔又补充道。
张一元想起小崔上午在局群的表现,有意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隐隐流露出对他的担心。小崔微微一笑,把手机推到张一元面前,点开一个页面。
是“永不止步”给他的私信:你在群里的发言很好,以后继续!后面是一个硕大的大拇指。
张一元颇为不解地望着小崔。小崔把手机收回,沾沾自喜地小声道,表扬领导,怎么会有错呢?关键是看准时机,掌握火候,对不对?比方一个人爱喝酒,喝多了,固然不好;你不让他喝,行吗?……哈,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世界,微信群,不也是个舞台吗?师兄,我说透了没有?
张一元傻傻地听着,终于回过味儿来,冲小崔竖起大拇指。
小崔端起碗喝口汤,抹抹嘴巴说,师兄啊,我瞎说,别当真。
那天合该有事。按照处里的安排,张一元要到广州出个短差。早上没睁开眼呢,李沐湘就因为鸡毛蒜皮的事跟他斗气。他赌气出门,早饭都没吃,坐上地铁,她还在发微信责怪他,话说得相当难听。他懒得搭理她。这种人,你越理她,她越是来劲,于是他就不去看手机。到了机场,办过登机手续,找到登记口,坐下来喘口气,拿出手机,点开本局公号和局群,看到局办一个多小时前发了一则通告:本局主抓的一项科研课题荣获国家部委奖励。
朋友圈里,同事们都在大力转发这则重大消息。“我爱我局”里面,更是嗨翻了天。因为这个项目是王局力推的,所以怎么表扬局领导都是应该的,感觉大伙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赞美局党委尤其是王局。
张一元有点怪自己,刚才应该在地铁上看一下局群的,都是被李沐湘气昏了头,否则的话,腹稿早打好了,祝贺的话早就发出去了,弄得现在有点被动。
果然,李处的私信来了,问他上飞机没有,赶紧到局群露个头,这么大的喜讯,不能无感啊!
他回复:一会儿上飞机,马上办。处长放心。
集中精力,思考了一下。尽量不要重复别人,尽量说点新鲜的词儿,这是小崔教他的……时间太紧,来不及细想,加上李沐湘今天跟他较上劲了,老是不停地发信埋怨他,所以凑合着先编了一条发出去,打算飞机上再琢磨一段有文采的,落地后立即发出。
登机,张一元起身排队。李沐湘又发来一条骂他的话,他气不打一处来,手指头哆嗦着打出一行字,气哼哼发出去:没完没了的烦不烦?真他妈讨厌!
随即,关了机。
三个小时后,飞机落地,张一元打开手机,一看,彻底傻了眼!
那句骂人话,竟然发到了“我爱我局”。可以想见,就像丢进群里一枚炸弹,把所有人都搞蒙了!
在那句骂人的话下面,好长一段时间无人跟帖。也许会有人私下偷着乐吧……李涛反应还算快,补发了一条帮他开脱:张一元现在飞广州的飞机上联系不上,肯定是误发了。我代表三处向局领导和全局同志道歉,太对不起啦!后面是一串流汗的表情包。
张一元满头是汗,顾不上拿行李,歪倒在座位上,哆嗦着发出一条更正加道歉的短消息。
他给李涛打语音电话解释。李涛丢下一句,回来再说吧。就挂断了。
尽管所有人都相信张一元是误发,是手误,不是故意。但这种糗事,在严肃的场合,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四处的老胡,曾经因为在局群发了一个带讽刺意味的表情包,惹得王局挺不乐意,让他解释是什么意思,老胡反复道歉才过关。
事情虽然出在张一元身上,李涛比他还紧张。李涛是个办事极认真极小心的人,平时处里开个小会,他都要求打印发言稿,挑错别字,反复纠正标点符号,遑论这么大的事。
李涛带张一元到王局办公室登门道歉,到赵副局那儿道歉,还到局办和其他几位处长那儿赔笑脸。事情总算过去了,李涛对张一元的态度,也是大不如从前了。
这之后张一元真像小崔说的,看手机上了瘾,随时盯着局群,整天提心吊胆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误事,更怕出错。他和妻子的关系,也是每况愈下。有几次,好不容易来点情绪想亲热一下,却因为手机闹动静,进行不下去。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阳了……不是新冠阳性,而是那个阳……阳痿的阳……李沐湘气急败坏把他掀翻。
从此就分床睡了。
次年年底,张一元和李沐湘领了离婚证。不久,他辞去工作,在家休息了一阵子。
又过了不久,王局得到重用,到下边的一个地级市当市长。孙副局从党校回来接班扶了正。据说孙局一上任就打听张一元,得知他办理了离职,退了群,摇摇头说,可惜了。
差不多此时,张一元重新找到了工作,到一家赫赫有名的私企上班。报到那天,主管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加微信,并且拉他入群。面目和善的主管拍拍他的肩膀,幽默地一笑,说,请君入群。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