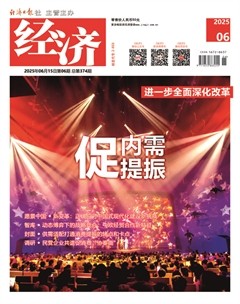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实现路径,并结合高质量发展规律进行了战略擘画和系统部署,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点明了动力源泉。当前,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一股强劲的向“新”求“质”浪潮正在各地不断涌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既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更是产业变革的“神经末梢”,具有实体产业基础庞大、资源能源禀赋突出、经济腹地广阔纵深等独特优势,是实现产业深度转型的主要载体,为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供了丰富的实验场景和转化空间,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空间载体。东部县域作为我国县域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增长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科学布局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挑大梁,既是其使命所在,更是其责任担当。
东部县域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前沿阵地
东部县域经济规模可观、产业基础扎实,拥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肥沃土壤。东部县域以全国约8%的县域面积、约20%的县域数量、约30%的县域人口,贡献了超40%的县域GDP、近45%的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2024年,“千亿县”总数达62个,东部县域占据46席,前10名中东部县域独占8席,头部县市昆山市和江阴市生产总值达5000亿元,超过中西部绝大部分普通地级市经济体量,晋江、张家港、常熟、慈溪、义乌、宜兴6县市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东部县域发达的工业体系主导作用持续发挥,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4省所辖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均超万亿元,河北省所辖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5000亿元,昆山市工业总产值已超万亿元,江阴市、张家港市、宜兴市、常熟市、慈溪市等工业总产值也均达到5000亿元规模。东部县域工业增长潜力巨大,近30%东部县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8%),龙口市、溧阳市、新沂市、乐清市、晋江市、福安市等县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超10%。
东部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产业创新成果丰富,构筑了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地。东部县域凭借人才、资本集聚优势,成为前沿技术落地“首站”,部分东部县域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常熟市研发投入强度超过4%,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太仓市、宜兴市研发投入强度也均超3%。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部分东部县域的主要增长点,余姚市、乐清市、义乌市、胶州市、长兴县、桐乡市、嵊州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60%,新昌县更是超过90%,均超过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昆山市、常熟市、太仓市、胶州市、乐清市、张家港市、江阴市7县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超1000家。依托完整产业链和资源禀赋,东部县域率先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跃迁,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渗透率显著高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昆山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超7000亿元,张家港市冶金新材料、太仓市高端装备、宜兴市电线电缆、晋江市纺织鞋服、福安市不锈钢新材料、乐清电气产业集群规模均已超2000亿元;江阴、昆山、胶州、溧阳、常熟、晋江、新昌、南安等发达县域在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东部县域深度嵌入产业分工、紧密参与产业协作,打造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协同生态。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东部发达的都市圈城市群正加速演变形成“核心城市突破—节点城市支撑—县域底座托举”的分工体系,实现研发在沪杭、转化在县域的协同模式(如长三角县域共建产业合作园)。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周边县域承接卫星城功能,发展“配套经济”(如海安市打造上海“北大门”物流枢纽、四会市建设广佛建材与物流卫星城)。东部县域经济带加速形成,跨县域产业链协作(如福建省83个县域164条重点产业链全省协同)提升整体竞争力,创新链上推行“飞地园区”模式(如杭州未来科技城在湖州设立产业基地),供应链上构建跨区域产业云平台(昆山—太仓集成电路云平台),价值链上实施税收分成制度(京津冀开发区联盟)。东部县域通过产业精准嵌套(如闽宁产业园)、技术适配性转移(如新疆智能灌溉)和制度型开放(如飞地园区),既缓解自身土地、成本压力,又激活西部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
东部县域培育新质生产力三大范式
东部县域立足良好的产业基础、突出的创新水平、合理的空间布局,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前线”,立足差异化禀赋,瞄准“环节突破—规模跃升—源头创新”的梯次目标,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共同构建东部县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范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