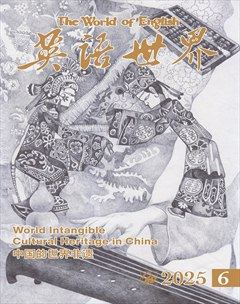论诗歌翻译的“王法”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翻译理论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有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奈达的交际理论,它们在我国粉墨登场,各有各的说法,而且无一不头头是道,其精密的系统和凿凿的言辞,令我国学者纷纷赞叹和皈依,就连资格深厚的老翻译家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有些专家学者哀叹道:“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
翻译界“欣欣向荣”的景象给西化的学者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以滔滔的势头逼退了“传统派”,叫资深的翻译家退避三舍,因为他们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和生花的妙笔,怎奈西化的学者说话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呛人得很,“传统派”根本不敢打擂台。这下子苦了翻译实践者,他们不知道该顺从哪个流派好,于是便依照自己的理解译将开来,只知道“忠实于原文”以及“通顺”即可。乱啊!错啊!其实,大部分译文仅仅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思,却枉顾内涵和延伸意思——这是一种倒退,翻译质量甚至还不如鲁迅的那个久远的时代,也不如我们建国初期(茅盾等优秀翻译家彼时在为我们掌握着航向),翻译出来的诗歌哼呀哈呀,非但没有了诗歌的相貌,就连意思也含混不清,读之如雾里看花。幸好我国及时地提出了“文化自信”(也包括翻译自信),才有了回暖的迹象。一些专家正本清源,开始郑重地提出了翻译的“规矩”(也可以称为“王法”)。谁都不愿当“违法之徒”,只是不明白何为“王法”嘛。
说实在的,若论翻译(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中国的确比西方强。早在公元68年,我国就建立了白马寺译经院。以后,翻译人才群星灿烂,有竺法兰、安世高等,玄奘(即唐僧)更是佼佼者。三国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支谦提出了“求信”“求达”的翻译思想,后经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严复梳理和排序就有了“信、达、雅”的原则。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英语世界》2025年6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