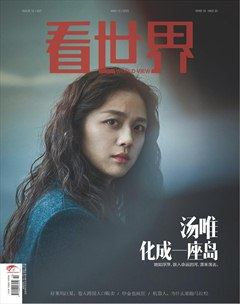今年3月,24岁的费宇小红了一把。走在街上,有人会突然跟他打招呼,或是看到他以后,和身旁的人悄悄议论起他的名字。有十几家媒体纷至沓来,关于他的报道铺在短视频和微博平台,最高的一条点赞量有50万。
费宇看起来是一个寻常的高校学生,留蓬松微长的发型,穿简单朴素的卫衣、格子衬衫,眉眼间透露着人们通常认为的、还没走出校园的清澈。
事实也如此,他已经在人生的田字格里规行矩步了20多年,完美地印证了一名杰出“小镇做题家”的故事模板:走出川南重重叠叠的大山,先是进入西南知名学府四川大学,而后顺着长江跨越半个中国,进入复旦大学深造读研。
故事在这里陡峭地转折。读到研究生的第二个学期,费宇出人意料地退学,开启了Gap Year(间隔年)。一年以后,他选择给自己找点事做,在川大校门口支起了一个卖土豆泥的小摊子—这让他为大众所熟知,并随着名校生摆摊的反差标签,登上热搜。
成为新闻事件的主人公后,费宇有一瞬间感到,全世界都在讨论他的这个选择。从亲邻的父母长辈、老师朋友,到网上的陌生人,说什么的都有。这个年轻的“00后”并不因此动摇,他对自己的决定很清晰、很坚定。
“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更多的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每年毕业生那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填不完的。我觉得,我可以代表这批脱下孔乙己长衫的人。”
费宇身上有着这个时代所留下的鲜明烙痕。小镇做题家最在乎的是答卷上的对与错,但在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塑造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准备出格一步,从川大校门外的一个小摊子开始,给出不同的回答。
摆摊
下午5点,川大华西校区东区北门外,各色小吃摊沿着人行道排成一溜,一眼望不到尽头。问起哪家是卖土豆泥的,福鼎肉片的老板娘说,人最多的摊子就是,很好找,“难得排哦”。
北门对面,的确有一条长龙。摊子还没踪影,60多名顾客已经排起了队。5点15分,费宇和助手推着一辆简易的小黑车(连招牌也没有),一路小跑而来,边跑边连声应对催促,“好的,好的”。
队伍行进得很缓慢,两个年轻女孩跺脚抱怨:“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来买土豆泥了!”慢是有原因的,小吃街罕见的长龙,和费宇本人在网络上的名气,吸引了不少人在摊子附近围观,“啥子情况哦?”他们举着手机,从各个方位拍摄费宇。比起卖土豆泥,这里更像是围观网红的现场。
费宇也在社交账号“华西食研室”分享做土豆泥的教程,视频的结束语是:“以上便是准备土豆泥的全部东西了,谢谢大家。”评论区有人说:“有一种答辩和小组汇报的感觉。”费宇一直都很擅长做学生,也有着一张堪称漂亮的逆袭履历—他在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以第一名的成绩保研到复旦大学,还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SCI论文。

在实验室里,他是一名精细的工程师,摆弄EP管、移液器,调配试剂,把它们做成精致复杂的数据。而现在,这双手被用来抬50斤新鲜土豆,剁葱姜蒜、青红椒、折耳根,给料汁勾芡,在料桶里翻搅食材。
他伸出双手,手上有一些青紫的瘀痕,和细小的伤口。“昨天削胡萝卜,削破了皮。碰水碰得多,长了冻疮,或者湿疹。我不太分得清。”这是一双白净的、不太适合干粗活的手。
对于费宇做土豆泥,和他本科同窗五年的小桥倒不觉得奇怪。去年10月,在退学之后的空窗期,费宇就告诉身边的朋友,自己想要试试摆摊。“他真的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也比较有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