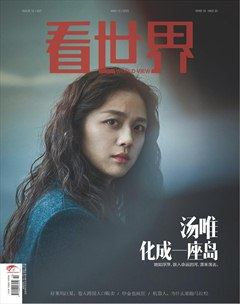樱花谢了的武汉,又因为公园里的一排椅子火了。东湖听涛景区的湖畔草地,多出了16把朝向湖水的躺椅。“欢迎前来躺平”—这是城市治理者向市民发来的邀请。
在今年的上海,去松江郊区或者苏州“0元挖野菜”的体验,战胜了人均几百元的Bistro餐厅,成了当代年轻人最新潮的约会方式。
南国广州,赏花之旅能从春天一直蔓延到第二年春天,开满天桥的三角梅和遍地灿烂的黄花风铃木、洋紫荆,让通勤之路都变得宜人了些许。
去年春天,“公园20分钟效应”忽然走红,一年过去,对这一概念的拥趸者规模愈发庞大,挑个晴朗的日子去公园“躺平”,俨然成了能与“元宵逛灯会”“中秋赏月”相媲美的风尚与习俗。
四季分明的北京,一到春天,公园就长满了人。
大风吹走了扰人的柳絮,周末的北京朝阳公园湖畔草坪,密密麻麻挤满了褪去西装的“精英”。有人独自前来,铺一张垫子,坐着读书,或躺着小憩。还有一家三口支起帐篷,躲在帘下打牌,只传来窃窃私语。笑声、歌声与微风鸟鸣,构成春日公园的底噪。
我曾亲眼在一座街角公园看见,一位具体年龄和性别难以分辨的中年人趴在一张瑜伽垫上,后背位置的衣料裸露敞开,在阳光下“晒背”。
还有一位网友发帖,在北京船坞公园,一位大爷支起板凳和露营桌,直接把书桌搬到了花丛间。
学者林峥把公园喻为“现代都市之心”。的确,没有什么场所比公园能更直观地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处境了:躺平也好、奔跑也罢,逃出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人们渴望在一个更趋近于原始和自然的场所获得片刻喘歇。
公园是一座城市对理想生活的回应。
城市需要公园
如今,武汉除了躺椅,还有72片共享草坪,允许游客在草皮上休憩、玩飞盘、搭帐篷。东湖在去年底播种了约32万㎡的黑麦草种,最大特点就是“耐踩踏”。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城市公园,悄悄撤下“禁止踩踏草坪”的标语,让市民真正亲近绿色。
但实际上,最早的城市是没有绿色的。18世纪末以前,以城墙为界,被圈起来的、光秃秃的灰黄色是人类居住的城镇,而之外被绿色覆盖的广袤土地是森林和原野。城墙内部即使存在零星的绿色,大都也是上流阶层的私人花园,普通居民难得一见。
如今,城市意味着一种便利和体面的生活,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早期工业化城镇却完全相反。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农民举家搬进城镇,在繁忙的纺织厂终日操劳。人口迅速膨胀,很快城镇就变得拥挤、狭小、通风不良,成了传染病肆虐的温床。
英国作家狄更斯,如此描写彼时城市的恶劣状况:“我看到疾病,扮着最丑陋的面貌和骇人的身形,在每一处巷子、小路、庭院、后街和陋室—每一个有人类聚集的地方,都取得了胜利……我看到无数人注定要走向黑暗、尘土、疫病、污秽、痛苦和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