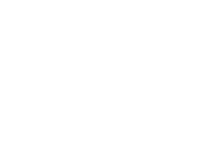2022年12月,营业近两年的成都浮于野书店突然宣布闭店,令人不胜惋惜。在接近锈带的读诗人群中,这家店靠读诗写诗、快速建立影响力,以极高的黏性在小众赛道成功巩固了一批阅读人口。
主理人刘大风两年后向《商界》记者道出这笔打不走的账:每月亏1万多到2万元,亏到30万元时,只能叫停了。
不过这是一次“兜”得住的失败。刘大风在正式关店前,用半年时间重新张罗了另一家店。眨眼的工夫,另一座浮于野书店高调宣布营业,经营面积竟是老店的近20倍。
浮于野本是国内几万家独立书店中的一个,仅靠个性化的选书营造阅读空间,吸引读者停留,购买产品。但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刘大风于是决定用一种反常规的模式重做一遍,说不定就通了呢。
一日扫地僧
2020年,受“书香成都”等政策刺激,成都迎来一批线下实体书店的开店热潮。在互联网大厂任职数年的刘大风长期泡在文化岗,酷爱阅读尤其是读诗,生平第一次有了开书店的想法。
他按自己的想法去选址,最后找到位于武侯区安居街约70平方米的一家门店。
至于书店名字“浮于野”,并不是刘大风取的。他介绍说,名字源于德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Flaneur”,直译为“城市漫游者”,结果被音译为“浮于野”。“朋友知道我要开书店,灵机一动,把它打在对话框里发给了我。”他一秒就看上了。
2021年2月14日,书店开业。

看上去,这家店有所有小店的特点,进货灵活,不存在多余人工,必要时24小时都能营业。由于只卖诗集和小众小说,老板对客情也能及时把握。为了兼顾时间,他还创新了顾店模式。
他没有把店长当成一个固定的打工人,而是将其活用为一个连接互动的岗位,设计成“一日店长”工作模式,用这个人把书店的阅读氛围和精神生活搅动起来。
店长不应该只会简单冲咖啡、擦桌子、收银,他应该是店里的精神坐标。曾在大厂文化岗担任要职的刘大风,在微信公众号、小红书等平台开始招募“一日店长”,邀请喜欢读诗的人来店里做“扫地僧”:每天用粉笔在小黑板抄一首自己喜欢的诗,可以随便读书柜里的书、喝饮品,关键每天还能领到150元工资。第二天,新店长须擦掉黑板上的旧诗,重新抄一首自己喜欢的,如此往复。
浮于野迎来很好的开场,“一日店长”引爆了参与度和门店人气。“来报名当店长的一度排了4 000多人。”刘大风说,要10年才能排完。
后来被不少精酿啤酒店模仿的“打酒师”模式,正源于“一日店长”。但刘大风不做噱头,在赋予店长多重福利基础上,坚持每天排期、更换,保质保量运营,将其践行到极致。
这样,365天坚持不走样。每个店长既是新的阅读纽带又是未来潜在的消费者,如此设计很快打响了小店名声,在特定的目标人群中迅速扩散。
接着,围绕主营的诗集,刘大风又操刀了第二场设计,迎来“双响炮”。
还是通过招募,刘大风组织了郊外读诗会,带读者把店里的诗集或自己写的诗拿到草坪上读,真正地放声朗读、交流。用镜头捕捉,再传播。一群人跟着他读了许多场诗。上一期读诗会产生下一期读诗会的运转人,就这样大约维持了30期。
然而,书友的天堂成了书店客单的地狱,刘大风很快发现问题。
烧掉30万元以后
浮于野是线下实体店,图书和咖啡饮品是主力商品。起初刘大风想用文化认同感极强的活动和书籍的零售强绑定,来抹平书店的运营成本。但经营几个月后,书店名气和经营状况背道而驰。“书,书卖不出去;饮品,饮品卖不出去。”刘大风回忆,每次活动都人满为患却看不到钱,根本产生不了营收。
对客人来说,这是阅读舒适区,进来就不想走了,刘大风非常欣慰。但问题是读得很舒服为什么要买走,那这样开下去是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他反复问自己,如果一直这样,书店能亏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