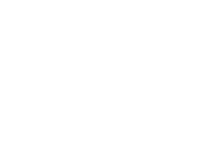人工智能工具的广泛应用,让企业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现实:如何重新理解组织、重新认识人力。
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员工适应的速度,企业要跟进吗?年轻、充满活力但经验尚浅的求职者不断涌入,企业要换人吗?商业环境变幻莫测,员工经验能力匹配不上,企业要重新培训吗?产品滞销、渠道不通,组织开始臃肿,企业只能裁员吗?
时至今日,许多管理者仍旧把人力当作消耗性资源,纳入企业成本核算体系。然而,这种因循守旧的管理思维,已被现代更灵活、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取代。在新型组织管理模式下,人力资源被视为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既是资本,更是企业的第二利润源泉。
人力资源应该是鲜活的,更应该是充满灵性的。上述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寻求解决方案本身,而在于对问题根源的认知。良好的组织管理机制,能够在问题萌芽阶段便将其化解于无形。
趋势
重新认识“人”的价值
“工具”到“智囊团”的转变,迫使企业治理思维转变。
马云曾说:“阿里巴巴最重要的产品是‘人’,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出干部’。”曾经的阿里,在技术层面不及百度,在产品领域也稍逊于腾讯。然而,自“十八罗汉”起,阿里巴巴便人才济济,其组织能力之卓越,不仅被许多互联网企业奉为圭臬,也被众多传统企业模仿和学习。
那么,为何我们如今要再次强调组织变革与人才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呢?原因在于,如今技术变了,商业逻辑变了。这就如同战场上的武器装备更新了、战场态势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架构与作战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同时,无论用户还是员工,95后、00后的崛起,让组织形式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变革。
把企业做成城市
在企业管理领域,一个常见误区是:人们往往认为互联网企业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是因为它们找到了更优的组织模式。然而,这一观点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是高速增长的业绩赋予了互联网企业组织模式更大的容错空间。
企业和生命一样,都有求生欲,有新陈代谢和自我复制的驱动力。相较于生命体历经数十亿年的进化历程,仅有几十年历史的现代企业就像个婴儿。这也揭示了企业并非一出生就携带生存本能和有效的免疫机制,同时,企业的组织形式,肯定会在商业环境和技术的变化中不断迭代和完善。
万变不离其宗。若将生命的存续与发展视为遵循“熵减”规律的过程,那么企业同样需要注入负熵以对抗大企业病。大企业病不仅是传统金字塔形组织的天然基因,“部门墙”“隔热层”“流程桶”等问题,在许多宣称自己是平台型组织的企业中,也反复出现。
因此,企业并无传统与互联网之分。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组织形式,终将走向“熵增”的末路,最终消亡。
凯文·凯利曾指出:“所有企业注定都难逃一死,城市却近乎不朽。” 城市作为分布式、自下而上、创新驱动的生态系统,其活力源自每一位居民。当城市平台能够激励并赋能每位居民时,便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生态体系,相互滋养。
所以,企业逃离熵增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于激发员工的潜能,而非依赖威权或流程来解决问题。威权是“一个人”的理性,流程则界定了颗粒度极细的规则。面对时刻变化的环境,无论是一个人的理性还是事无巨细的规则,其应变能力都不会太强。随着企业规模变大,其管理思维必将趋于僵化。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应变能力关乎生死存亡。所以,企业能否将自己打造为“城市生态”,激发每位员工的潜能,让人人成为自己的“CEO”,也许将成为未来商业竞争的“决战之地”。
科技的狂欢和隐忧
任何组织的构建均围绕两大核心要素展开:人与任务。传统管理理念始终聚焦于如何协调人与任务的关系,涉及诸如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团队协作以及动机等议题,均着眼于人与任务之间的协调关系。
技术的迭代、商业环境的变化,以及教育带来的年轻群体个性、精神的释放,让人与任务之间的关系从线性变成了互动式结构。很难再用单一的任务去绑定一个年轻人数年。他们往往需要更多的柔性空间、更大的自主权、更广阔的创造力空间和更具趣味性的工作环境。

这一转变随着生成式AI的加入愈发显著。人工智能首次实现了人与AI之间的协作互动,使交流从单向转变成双向,打通了人、任务(工作)与AI(自动化)之间的闭环。
今年上半年,一份全球职场AI应用调研报告公布,揭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数据。其中,高达96%的职场人士认为生成式AI对工作具有巨大助力。当前,全球科技巨头如微软、谷歌等正实施瘦身计划,将更多资源投入AI工具研发中,AI的赋能将使每位员工蜕变为超级个体,拥有无限潜能。
诸多知名的超大型企业如华为、海信、吉利控股等,得出的结论是AI正在全方位重塑人力资源管理,并将在重塑组织、革新岗位、升维劳动力、提升人才密度、加速人才流动以及驱动数字化工具的迭代六大方面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以华为为例,其未来组织架构将向大平台支撑下的精兵作战模式升级。简单来说,华为已从传统职能型组织架构转型为以项目型为核心的组织架构。AI的赋能,将进一步推动企业组织架构的迭代与升级,比如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他们变成了大中台、小前台的模式。
当AI能够承担80%的重复性工作时,员工的价值将由“被动完成任务”转向“主动定义问题”。未来组织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将聚焦于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以及跨领域知识整合,而非单纯的技能熟练度。从“管理人力”到“经营人才价值”,从“流程管控”到“生态赋能”,从“稳定结构”到“动态进化”,随着AI成为基础设施,真正稀缺的是人类的思考深度。这正是人力资源管理在新时代的价值锚点。
案例
微小而巨大
海尔小微模式让员工成为“创客”,直接分享市场收益。
2010年前后,海尔遭遇了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的冲击:用户需求日益个性化、市场竞争愈发碎片化、组织效率持续低下等问题层出不穷。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使得决策流程冗长烦琐,员工缺乏创新动力,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
海尔创始人张瑞敏提出“企业即人,文化是魂”的理念,主张传统企业应向“平台型组织”转型,通过“人单合一”(即员工与用户价值紧密结合)模式激发个体创造力。这与德鲁克“人人都是CEO”的理念不谋而合。
2013年,海尔北京工贸公司率先转型为“商圈小微”,从被动执行总部指令转变为主动挖掘用户需求,标志着海尔小微模式在销售端的初步尝试。
为坚定推进组织转型,海尔于2014年裁员1.6万人,2015年上半年再裁5 000人。这2.1万人中,除部分被淘汰者外,大多数加入了当时的169家小微公司。
高如强曾是海尔青岛服务中心的一名内勤,负责网点派单、调度送货。后来,他与搭档合伙购车,加盟海尔物流配送系统,成为“车小微”的一员。他们每日抢单、送货、安装、维修,收益按比例分配。“我现在平均每天接单四到五个,加上车的成本的话,平均每个单子至少净赚60到70元。买车花了2万元,基本两个月之内把买车的投入都赚回来了。”高如强说。
“车小微”隶属于海尔的日日顺平台,该平台整合了海尔原有的6 000多家服务商的送装服务,并吸引了数万社会车辆加盟。他们通过互联网自主进入,自主抢单,服务评价来自用户,考核则靠信息系统。这些配送车辆既可以承接海尔的配送单子,也可以承接阿里巴巴、京东或者其他任何品牌商的配送单子。
小微模式让员工成为“创客”,直接分享市场收益。例如“雷神”游戏本团队,由3名员工发起,通过用户互动开发产品,两年内销售额突破7亿元,并成功吸引3轮外部融资。
海尔小微模式的具体做法包含4个核心机制:
1.组织重构:从金字塔到“热带雨林”生态转型
张瑞敏把海尔划分三类主体:平台主(资源支持者)、小微主(创业团队负责人)、创客(执行者)。小微可自由组合为“链群”(生态协作单元),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例如,郑州冰箱销售小微与合肥制造小微联合成立链群,实现“零缺陷、零延误”目标。
2.员工创客化:让打工者变老板
小微群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利益绑定机制,员工须出资持股(如雷神团队初期自筹资金),收益与市场表现紧密挂钩。海尔郑州某链群约定:利润增长30%可分享23万元奖金。同时,设立淘汰机制,未达对赌目标的小微将被解散。例如,某清洗服务小微因用户复购率低于50%而被淘汰。
3.平台化支撑:资源“按需取用”
海尔的小微经济模式,是建立在海尔强大的供应链和产品链上的创新,拥有三大赋能平台:HOPE平台连接全球研发资源,每月产生500+创新方案(如“冷宫”冰箱源于粉丝互动);海创汇提供资金和孵化支持,累计投资上万项目;日日顺物流的“车小微”通过抢单模式服务海尔及外部企业。
4.建立动态考核体系
海尔建立了二维点阵评估:横轴考核市场业绩(如销售额),纵轴考核用户价值(如复购率、满意度)。另外,海尔还以用户付薪制倒逼服务升级。例如,某冰箱小微承诺“24小时送达否则免单”,促使服务优化,投诉率下降40%。
海尔的小微模式对传统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转型有典型的参考意义:(1)打破边界:例如,服装厂可借鉴海尔经验,将部门变为创业单元,让设计师成立“时尚小微”,直接对接网红直播间。(2)重构激励:如快递公司用“增值分享”替代固定工资,按区域满意度排名发放奖金。(3)生态共建:学“车小微”模式开放供应链资源,让社会车辆加盟物流网络。
人力从成本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在于用机制释放人的创造力,而非单纯依赖技术或资本。正如张瑞敏所言:“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不是机器,而是能持续创造价值的人。”
“无限放假”生产力
知识型工作成效难以单纯以时间作为量化标准,而创新成果往往诞生于非结构化场景。
Netflix(奈飞)作为全球领先的流媒体服务与内容制作公司,在管理创新方面有着诸多值得探讨之处。
2004年,Netflix一名员工提出疑问:公司既不对每日工作时长设限(如周末处理邮件、非工作时间办公),为何还要计算休假天数?这一质疑,揭示了工业时代“时间管控”与知识经济“结果导向”之间的矛盾。
互联网时代,知识型工作难以用时间量化,创新往往诞生于非结构化场景(如休假时的灵感迸发)。同时,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管理模式(如固定工时、考勤制度),已无法适应脑力劳动的需求。
基于此,Netflix创始人Reed Hastings提出“成年人管理哲学”,认为优秀员工应被赋予自主权。其核心假设是:自由与责任互为因果—当员工拥有决策权时,责任感反而增强。无限休假制度便是这一理念下的重要管理制度之一。
当时,Netflix取消了传统的固定休假天数限制,宣布员工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和工作安排自由休假,前提是确保工作成果不受影响。整个过程无审批流程,员工可随时休假,无需上级批准,仅需提前与团队沟通(如财务部门在忙季须提前报备);并且可以弹性定义休假,涵盖传统假期、病假、个人事务处理等场景,避免形式化分割。
然而,无限休假制度实施初期, Netflix的管理层发现,许多员工因担心被视为“不够努力”而不敢休假。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司鼓励高管带头休假,以树立榜样。
Netflix相信,过度管理会扼杀创造力。无限休假鼓励员工自我管理,从而专注于产出而非出勤时间。这种文化催生了《纸牌屋》《怪奇物语》等现象级作品。取消休假跟踪系统简化了人力资源管理,省去了烦琐的审批流程和假期余额计算。无限休假还成为Netflix“前卫”文化的象征,提升了其在全球雇主品牌中的竞争力。
但无限休假制度并非放任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