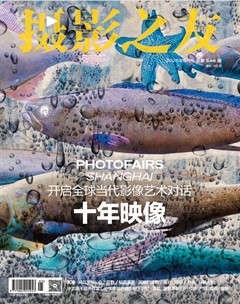游荡者未必迷途 周仰
托尔金和他创造的中洲世界,用美作为抵抗黑暗的武器,像明亮的星一样,震撼了摄影师周仰的心,照耀了跨越时空奇迹般相遇的时刻。从此,她的作品里总是有托尔金的影子。《一颗星照耀着我们相遇的时刻》是她对这位传奇人物的致敬,他提出的“次创造”理论成为“不朽的林泉”系列的基石。2022 年,重返英国读博后,周仰开始探访“托尔金的足迹”,在当代艺术羞于谈“美”的时代,她在游荡与朝圣的路上,也在寻找一条关于摄影美学的路。

“那颗星的美震撼了他的心,当他从这片被遗弃的大地抬头仰望,希望又回到了他心里,因为一种清晰又冷静的领悟如同箭矢一般,直透他心底——魔影终归只是渺小之物,且会逝去,而在魔影无法触及之处,光明与崇高之美永存。”
—— 托尔金,《魔戒》,卷六第二章


INTERVIEW
摄影之友×周仰

托尔金对您和您的创作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托尔金的作品?
周仰:2001 年《魔戒》电影上映,当年是看了的,但也只是欣赏电影,2000年左右的原著翻译得实在太差,虽然读了,却没留下什么印象,以至于直到 2013 年我才命运般地与原著重新相遇——那年我在英国短暂停留,其间有一天突然像是被“植入”了一个念头,要去伦敦查令十字街那些旧书店里寻一套原版的《魔戒》三部曲,刚巧就找到一套三本不同版次的,之后读了,就非常着迷。
大众对于托尔金的了解可能更多还是在文学方面,但他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是极深的。您认为他的语言学研究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周仰:其实托尔金的专业是 philology,应该翻译为“语文学”,主要研究古代语言,和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非常不一样。他对古代文本的研究,比如古英语的《贝奥武甫》、古冰岛语的萨迦、古代日耳曼神话传说等,其中很多元素都被吸纳到中洲里面。当然更不能忘记他创作中洲神话体系等目的之一就是为他发明的精灵语提供一个语境——托尔金曾经在一封书信中提到,他写《魔戒》的原因之一是要创造一个情景,让“Elen síla lúmenn’omentielvo”(一颗星照耀着我们相遇的时刻),这样一句他发明的精灵语能在其中成为一个打招呼的用语。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摄影之友》2025年5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