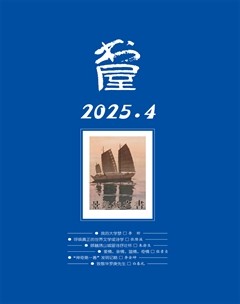2013年7月20日,我到美国西雅图看望读书的儿子。正值盛夏,西雅图的天气有点阴沉,气温很低,早晨起来居然颇有凉意,仿佛我们国内的深秋。西雅图的天气呈现两极化的现象。夏天是旱季,雨量很少,晴空万里,看不到一丝云彩,地上的草也开始变得枯黄。冬天是雨季,因为雨量丰沛,草坪反而显得碧绿碧绿的。然而每次下雨的时间又不会太长,往往一阵雨过去,天空便呈现湛蓝的色彩,仿佛童话世界。冬季云层丰富,站在傍晚的海边,大半个天空仿佛燃烧的火焰,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太真实。
儿子租住的寓所距离华盛顿大学很近。那时我正在收集有关梁实秋的资料,他晚年曾在西雅图居住,女儿梁文蔷也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工作过。或许,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与档案间,还能寻觅到梁实秋父女的些许踪迹。
华盛顿大学的校园也是一派古树参天的景象,可惜现在不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图书馆门前的樱花树早已变得郁郁葱葱,与樱花盛放时相比简直判若两树。梁实秋晚年在回忆青岛的文章中提到西雅图的樱花:“虽然也颇可观,但究比青岛逊色,我有同感。”
首先便去拜访华大东亚图书馆的馆长沈志佳博士。我知道,在美国任何拜访都需事先预约,因不知道沈博士的电话,无法预约,只得冒昧前往。沈博士曾任科罗拉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梁实秋早年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而王小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匹兹堡大学留学,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做过王小波的老师,而沈博士曾兼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其中或许蕴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渊源,值得细细探寻。
九点多钟,我见到了沈博士。沈博士刚刚送走了一个预约实习的大学生,我很抱歉地做了自我介绍。沈博士非常热情,她说欢迎世界各地的学者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如果学者出了学术成绩,只需要提及他们的图书馆就好,她说,那样图书馆也脸上有光呢!
聊天中得知,沈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图书馆专业,获硕士学位。巧的是,沈博士老家是济南,与我算是老乡了。
2012年冬天,我第一次到访西雅图。冬季的阳光温和而低调,天空呈现出深邃的湛蓝色。
西雅图海岸线绵长,湖泊众多。冬季暖流恰到好处地途经此地,潮湿温暖的空气遇到奥林匹克山脉,攀爬,升华,凝结成雨,造成西雅图冬季多雨的气候。
仿佛还嫌不够似的,那环布四周的火山与雪山更为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猛一抬头好像就要与它们撞个满怀。
1972年,梁实秋决定“卖掉房子,结束这个经营了多年的破家,迁移到美国去”。当年5月,他卖掉台北安东街三零九巷的寓所,携夫人程季淑投奔西雅图的女儿梁文蔷。其间,夫人程季淑过得并不开心,言语不通,不敢与邻居说话,看不懂电视,不敢独自进店铺,罹患高血压的她只能以织毛衣打发时间。梁实秋依然每天四点多钟起床,手执一把雨伞,外出散步,风雨无阻。上午则陪夫人到超市买菜,中午下厨小试身手,下午读书写作、翻译文学作品。
然而1974年4月30日,死神竟然不期而至,突然攫去了程季淑的生命!上午十点,梁实秋和夫人像往常一样手拉手前往超市购物。一阵风吹过,超市门口的一个梯子倒了,正好砸在程季淑的头上,急送医院抢救,可惜不治身亡。“我说这是命运,因为我想不出别的任何理由可以解释。我问天,天不语,”梁实秋在《槐园梦忆》中写道,“不是命运是什么?人世间时常没有公道,没有报应,只是命运,盲目的命运!我像一棵树,突然一声霹雳,电火殛毁了半劈的树干,还剩下半株,有枝有叶,还活着,但是生意尽矣。两个人手拉着手的走下山,一个突然倒下去,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的独自继续他的旅程!”
1974年8月29日,梁实秋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悼念文章《槐园梦忆》,文中回忆了程季淑含辛茹苦的一生,以及他们的相识相知、悲欢离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虽然平凡,读来却感人至深。“重壤永幽隔”“徘徊墟墓间”,以至于他希望人死后尚有灵魂,“夜眠闻声惊醒,以为亡魂归来,而竟无灵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