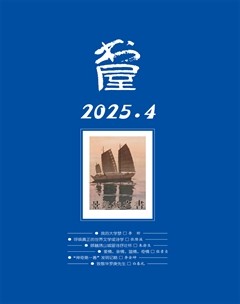陈家琪,教授,著名哲学家,曾担任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及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西方哲学学者之一,已出版《愿作如是观》《三十年间有与无》《话语的真相》《人生天地间》《持存记忆》等。
陈宣良,旅法学者,著名哲学家,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中文译者,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关注中西文明对比,已出版《中国文明的本质》《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等。
芦苇,原名张焰,作家,文艺评论家,出版《异乡人之书——芦苇散文集》,在《长城》《书屋》《作家》《中文学刊》等多家报刊发表小说、评论、散文等作品数十篇。
2024年初秋,巴黎还在不紧不慢地拆除临时搭建的各类奥运场馆。塞纳河上,一根根高柱还牢牢地扎在水里,让人想起不久前的奥运会开幕式。法国人的浪漫与创意颠覆了人们对奥运场景的想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其出格之处也备受质疑)。在幽静的河边小径上,有几个游客停下脚步,蓝蓝的天,白云飘在古建筑的上方,游船缓缓地开着,开到每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去。噢,这真是一个适合沉思的地方。望着高柱投在河水中的阴影,不曾觉察到的记忆就这样在心里生根。对于有的人,记忆是死去的树、死去的花,记忆是焚烧后留下的一团灰烬,风一吹,就没了。但对于有的人,记忆是故事重新开始的地方——正在巴黎度假的陈家琪教授对此感触颇深,他背着记忆走得很累,他总想说出不可磨灭的东西。这次来巴黎,我参加了与《五十年间有与无》有关的一个座谈会,并对陈教授及其密友陈宣良先生做了三次访谈。
两位先生的神情、手势以及彼此间的默契一瞥,都与他们犀利敏锐的谈吐融为一体,这是两位历经坎坷却依旧清澈如山泉的人,也是两位精神强大的人。前几天,他们在爱丁堡的休谟雕塑前久久徘徊,不舍离去。他们频繁地交谈(一切)——他们的对话——我相信还会一直继续下去。我无法抓住每一句话和每一次的会心一笑,我无法看清两颗悲怆心灵的形状,我甚至不得不忽略法式咖啡的浓郁、薰衣草的香味和巴黎圣母院旁的落魄眼眸,但我希望,我已经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了。
芦苇:家琪老师,先祝贺你的新书出版。你一直对书写记忆情有独钟,事实上,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这个问题,你的文字带来很多启示。《五十年间有与无》才出版不久,《持存记忆》又问世了,依然是对记忆的守护。我很喜欢“持存”这个词。你一直努力记录、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坚持触碰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化景观——在一个擅长遗忘的年代,你如何承受这种孤独?
陈家琪:一开始不是用“持存”,最后我选定了这个词。我要把自己能够看到什么、思考到什么程度如实记录下来,给未来的人看。这个事得有人做,对于一个一辈子从事哲学的学者,仅仅记录当然还不够,必须有思考的厚度。至于说承受孤独,人反正都是孤独的。昨天座谈会上,我也谈到了把《三十年间有与无》扩充为《五十年间有与无》,是为了纪念我的妻子李少华,我和她从1968年开始相恋,到她2018年去世,刚好是五十年。你未见过她,真让人无法忘怀。
芦苇:那本书的第一页——你和夫人的那张合影好美。你的书将让她永远美下去。座谈会上,你泪洒现场,前排的女孩眼圈都红了。
陈家琪:因为我想起了李少华。在《持存记忆》的扉页中,我将这本书献给了她。
陈宣良: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无奈。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这个结局都没有办法改变,而我不能接受这个结局。这就是一种无奈。
陈家琪:我这个人吧,一辈子离不开一个字,“情”。情谊、情义中的“情”,当然还有爱,爱情。我活在过去。
芦苇:因为你喜欢将哲学史的问题绕回到你最看重的“情”这一点上,即绕回个人的情感上。我觉得你的意图是这样的,启发人们把哲学问题变为个人问题,在不可抗力中寻找出路。
陈家琪:我一直在尝试。把当代的问题不仅仅看作是理论问题,而是把它变成自己的生存问题,把时代的大问题变成个人的问题,于是无法安宁,寻找个人的解决之道。
陈宣良:到了那种时候,他害怕自己忘掉。不忘掉很痛苦,但是又害怕忘掉。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理性和逻辑的。讲到家琪的感性,他的确是感性的,这恰恰是他和(邓)晓芒的性格差异,因为晓芒是理性的,因此,家琪是综合的,晓芒是分析的。家琪喜欢从价值论出发透视知识论,而在晓芒那里,知识论是他看待问题的出发点。
陈家琪:衰老到无法进行思考,这比死亡可怕。说到死,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已经不怕死了。真的,无所谓了,在这个年龄已经不在乎了。失忆另当别论。失忆的人无法再把握自己的时间。霍夫曼主演过一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阿尔茨海默病与时间有关,时间混乱了就证明人痴呆了。时间让人只剩下回忆,但时间也没有尽头。我刚才讲我这辈子离不开“情”,另一样我这辈子离不开的东西就是手表。我的时间观念很强,永远戴着手表,从小到现在,从没有迟到过一次。除了洗澡,我连睡觉都不脱手表。
芦苇:存在与虚无,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家琪老师,宣良老师说你喜欢从价值论透视知识论,你能不能谈谈存在主义哲学的价值观?
陈家琪:萨特的价值观,核心是人的选择,即“你所挑选的意义”。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悲观的学说。全部的伦理学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对于任何人来说,是否存在着一个人格完善或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你可以视为人类的模型。在宗教哲学家那里,这个模型用上帝来表示;在传统哲学家那里,这个模型是对于人的本质的概括。这样,当哲学家把目光放在人身上时,脑子里会先有一个与人的共同本性有关的概念,这叫本质先于存在。但是,存在主义说,人并没有一个先天存在的本质,因为每个人的未来不是像植物生长那样,从种子就可以判断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懦夫和英雄并非天生,这就叫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说,本质先于存在和存在先于本质,都是形而上学。我们争论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的先后,也都是类似的争论。
陈宣良:“无”是有的,“有”是无的。萨特《存在与虚无》的最后一层意思说,人生是是一个洞。洞是什么?是“有”的“无”,比如碗、杯子等。萨特说人生所有的乐趣就在于填洞。吃,不就为了填饱肚子嘛。最理想的洞就是这样的:它看起来不是洞,但实际上是个洞,他甚至拿女阴做例子。这也符合他的那些何为人生乐趣的观点。
芦苇:所以享受情爱的过程也意味着对“无”的探险,在爱中,“无”是没有办法被填满的——但这也意味着相爱的人能从中获得不同寻常的充实感。宣良老师,你的人生可谓波澜起伏,你翻译的《存在与虚无》,还有《中国文明的本质》,都是无可替代的,我好羡慕。采访你,就不免联想到你的父亲——著名哲学家、翻译家陈修斋先生,当然,我最先想到的还是《存在与虚无》。作为萨特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你深刻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启蒙的著名学者,而且,这本出版于1987年的书至今都没有其他的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