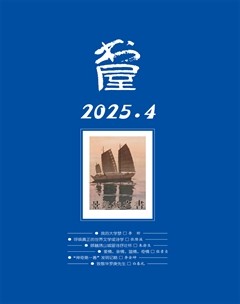探讨现代旧体诗人如何看待新诗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其态度往往比较隐晦,甚至自相矛盾。而钱仲联对新诗的看法却较为鲜明,他基本上认为当时的新诗不足以成为中国诗未来的出路。他在1926年4月《学衡》第五十二期发表《近代诗评》,历数自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名家,论其特点与短长。谈到新诗时,批评其“下至揉杂俗腔,标榜新派,《尝试》《草儿》之集,《女神》《湖畔》之编,僭据诗坛,见悦市贾,斯更等诸曹郐,略予攻弹”。他在1937年1月《学术世界》第二卷第三期发表《十五年来之诗学》,再次批评新诗:“此十五年中,有所谓白话新体诗者。胡适之(适)《尝试集》为其开山,刘大白、刘复、俞平伯、康洪章、郭沫若、徐志摩诸家继之,固亦从事于诗体解放者也。然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大雅所弗尚也。”不过他同时也指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这十五年,“诗体解放”已然成为潮流:“此十五年中,实为诗坛转变之枢。论其趋势,则由模仿而进于创造,由束窘而进于解放。而其成熟之果,则尚有待于将来焉。”钱氏所言非虚,关键是如何改变。他说十五年来的诗体解放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解放而未溃古人之围而出”,另一种是“尽抉诗之樊篱而破之”,前者如孙雄、王逸塘、杨圻等人的旧诗,后者即胡适、刘大白等人的新诗。他认为这两种解放途径都不理想,唯一认可的是“以旧格律运新意境”。但他又指出,如吴芳吉的作品,“有意以旧格律运新材料,然诗工太浅,所作芜秽庞杂,不足成家”。所谓“诗工太浅”即指吴氏诗不擅长使事用典。在另一篇文章《浙派诗论》中,钱氏追溯了清诗中浙派的源流,进一步指出:“今更当为进一步之革新,以浙派诗人艺术上之手腕,运新旧境界于一,必能光怪陆离,为诗世界拓新天地,则后起群贤,不可不勉也。”同光体浙派的突出特征就是“万卷撑肠,预之以学”。“运新旧境界于一”,也即用旧的典故反映新的现实,两者结合,即代表了钱氏的诗歌理想。
钱氏晚年自述受到陈衍、夏敬观、李宣龚等同光派诗人影响,并说近代以来最为佩服沈曾植。他说自己虽并非“同光体一派”的诗人,但早年就有志于“张新浙派之帜,本子培不坏一法不取一法之恉而光大之,为诗世界开辟新天地”(《十五年来之诗学》)。他曾质疑陈衍提出的“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说法,认为同光体闽赣派中多非学人,唯浙派的沈曾植方称得上真正的“学人之诗”。钱氏为最难懂的《海日楼诗》作注,在自序中认为沈氏远超朱彝尊、钱载,近逾陈三立、郑孝胥,高度评价其“括囊八代,安立三关。具如来之相好,为广大之教主”(《沈曾植集校注·自序》)。钱氏自己也学殖深厚,博文通史,可以算是同光体浙派当之无愧的传人。
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残酷的现实也使钱仲联关注到诗界革命派,笺注《人境庐诗草》的工作也正是在此之后逐步开展,到1936年正式出版,与他大量书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正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