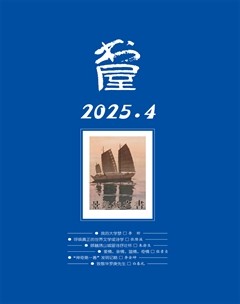聂华苓这个名字
2024年10月21日,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逝世,消息传来,我看着书架上的《三生三世》《三十年后:归人札记》《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等书,怅然若失,年少时的阅读场景,前尘往事,纷至沓来。如今○○后的学生们,很少提起三毛、柏杨、金庸、琼瑶,聂华苓对他们来说,好像就只是一个作家。更不必说聂华苓过世的当日,除了公众号与朋友圈之外,在台湾也只有几位文坛耆老发了些悼念文字,只是这些人皆已垂垂老矣。听他们再讲起《三生三世》,或许流风遗躅俨然如在,却也“旧江山,浑是新愁”,终不似少年游了。
二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到聂华苓这个名字,是从李敖的书上。当年服兵役时,每个月可以领到五千块台币(大概一千多元人民币),收入不多,买书却很豪迈,只要放假,就会骑着摩托车,花上四五十分钟,跑到还未拆迁重建的光华商场。一楼卖着各种3C产品及配件、电玩游戏,至于那些旧书摊则群聚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那是淘书人的天堂。我热衷到此,在透着霉味的斑驳墙壁下,摸着灰黄不一、或有书页脱落的旧书,习惯性地先擦去封面的薄尘,一本接着一本挑选着李敖的书。而平日省吃俭用,终于买了套四十卷的《李敖大全集》,从头细读,连书信、语录、讼状都不放过。那是个“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年纪,同时也从李敖书中看到无数的近当代人物,从刘福增到韦政通,从陆善仪到胡因梦,从《文星》到其他。我顺藤摸瓜,从点到线而面,把多数李敖提到的学者、文人,把能找到的书、能读到的文章,都看了。聂华苓当然也在其中。
受到李敖的影响,当时阅读聂华苓,更关注的自然是她与雷震、殷海光的交往,还有他们所办杂志的种种,以及她不愿意为胡适接机献花之事。随着年纪渐长,读书愈多,知人论世,李敖渐从我的阅读生命中淡去。“李敖书中提过的人”,痕迹渐消,反过来,当心中的偏见与滤镜消失,这些人的主体性反而可以凸显,我更能无拘无束地“享受”“静观”这些学者文人的人生、思考以及文采。只是没想到,春秋代序,一转眼间,胡秋原过世了,李敖不在了,聂华苓也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那些在我们年少时影响了我们、感动了我们的人,就像纷纷白雪飘散落下,好似无踪无迹、无消无息,却已在我们的生命中化成春水,不知不觉。或许在未来的机缘巧合中,一个暗示、一种象征、一个提醒,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会重新想起他们的书、他们的影子。
赶路的人们
在华语文学的舞台上,聂华苓的自传、小说、访谈都是很特别的存在。她的文字,时而喃喃自语,琐碎却也动人;时而诉说苦难,三生三世,却在不远处,仿佛若有光。她既专注个人又关心群体,她跟她笔下的铃子、桑青与桃红、翁莲儿,与父母、家族、移民、老百姓、近代中国之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交织着天真与堕落、故国与乡愁、丧失与获得、自我认同与性别意识等。正是因为这份特质,在学者眼中,离散、回望、女性、创伤、忧患,已成了研究聂华苓的主题,就如苏童所说:“聂华苓拥有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但她真挚从容的书写疏离了传奇,重在倾诉。聂华苓经历了苦难,但她坚韧的性情使她与苦难达成了和解,只留一份备忘录。”因此,不论是错综复杂的情感描写,还是祸福难测的人物命运,她的人生自传或小说人物,走江湖,入世间,涉人际,自诸妄想,或辗转相因,否泰有命,或通塞听天,其实都是聂华苓生命的备忘录。
正如聂华苓在《三生三世》中所说:“天茫茫,地茫茫,天地之间,只有那赶路的一溜人。”“人走多远,那沙幛就扯多远,没人说话,都在赶路。”对的,赶路,大家好像都在赶路,为了生活,不由自己,在时代潮流中被逼着前行,个人微小渺茫的生命,在麻木与糊涂之中,感受清醒的苦。历史如同立体而多层次的“盗梦空间”,时而繁杂有秩,时而混乱脱序。人际的互动,文化的交融,苦难与战乱,诸多忧患,蕴藏在繁华与衰败的节奏之中。聂华苓的人生与小说里,住着活生生的人。聂华苓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桑青变成桃红,她们都一样,经历内战、围城、赴台、入美;翁莲儿从美国到中国,从异乡到故土,千山外,水长流……她们也在赶路,走着走着,是豁然开朗,亦是九曲回肠,总似没有尽头。欲望有多深,理想有多真,路途就有多远。
就我看来,“行路难”也可说是聂华苓关心的主题。她对于感情、时代的独到见解即源于此。在她的笔下,爱与痛、无常与秩序,组成如织的密网,就如她自己所说“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丧失感”。在她的网内,许多语境与情境都是有意义与象征的,借用纪尔兹引用韦伯的话,顾名不思义:“人类是一种将自己置于自身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意义之网,正是聂华苓的行路旅程。
行路难,多歧路。1936年,父亲聂怒夫殉难,两房吵着分家分产,争得面红耳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