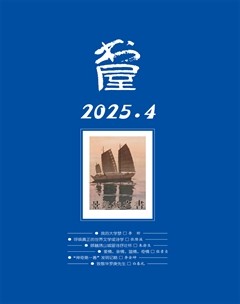话说当年三联书店首次引入董桥作品,以“读书文丛”出版了两种董桥作品《乡愁的理念》(1991)和《这一代的事》(1992),附收了柳苏先生原先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1989)。柳苏是罗孚的笔名,在北京居留十年期间和《读书》结缘颇深。2013年,李昕在三联总编辑任上支持饶淑荣出版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为推广宣传,李昕在微博上发文《你一定要读王鼎钧》,引起媒体舆论关注,“王鼎钧热”迅速升温,四部曲大卖超过十万套。而今轮到我来写李昕印象记,趁着春节假期,翻出李昕的十二种已版图书,读到快意处,不敢藏私,不甘专美,忍不住也要效颦罗孚,扯嗓门大喊一句:“你一定要读李昕!”
这么写这么说,一是因为和李昕太熟悉,二是因为他的书真的好。从2005年他到三联书店工作,我们开始共事,朝夕相处九年。2014年,他退休,被商务印书馆返聘,两家出版社南北相距不到九百米,我们还是常见常聚。2021年,我调到商务工作,再次聚首为同事。前后二十年,可说相知相契,无比熟稔。李昕退休后,从“为他人做嫁衣”,到“为自己量体裁衣”,从2015年横空出世的《做书:感悟与理念》,到新近出版的《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的时代》(以下简称《翻书忆往正思君》),十年间出版了十二种个人专著,包括繁体港版和简体内地版。用编辑的眼光和好书的标准衡量,可说部部都精彩。这些书我都放在身后书架上,和三联前辈邹韬奋、范用、沈昌文诸先生的作品放在一起,时常翻读,而且为他的书写过序言和推荐语,写过书评,还曾应邀作为嘉宾参加过两场对谈活动。
我与我的世界
李昕的这篇新作《我的大学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和主题写出了他的九年知青生活,除了清华园生活和家庭片段与他的《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略有交集之外,这是他的已版作品中少所涉及的一段青春往事,因此也不妨叫作“我的知青岁月”。他过去的写作,我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偏于编辑和出版的经验,谈做书的感悟与理念,可归入编辑学,适合做编辑出版培训;另一类是侧重出版史或回忆录,讲述书与人的故事。如果粗线条地概括的话,这些书都是聚焦他大学毕业后四十年的出版生涯,前者是有书无人,后者是有人无我,不免有“大公无私”之感。比较而言,只有这篇《我的大学梦》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聚焦于自己的知青生活和贯穿其间的“大学梦”,第一次进入“有我之境”。而且这篇文章是首次把回忆录系列的时间线往前推到青少年时段,也就是1969年十七岁到吉林白城洮安县下乡插队,到1978年二十六岁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近十年,我是把它当作李昕自传或回忆录的“前传”来看的。读完之后,又不免得陇望蜀地期待他接着写大学四年的回忆录。那自然是许多人都写过的题材,武大在那个时期也是有故事的名校,故事也精彩,如他的同学喻杉曾写过《女大学生宿舍》。相信李昕写他的“男大学生宿舍”,也一定值得期待。如此,他的回忆录才能在时段上形成完整的闭环。
《我的大学梦》中有三个故事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他从家里抽屉里找到户口本,没和父母商量,就偷偷地跑到派出所把户口迁到吉林农村,那个洮安县我是第一次听说。李昕从小在清华园长大,读书在清华附小、北大附中,放着颐和园也可以“插队”的选择不要,却一脚迈到东北黑土地的农村,这固然有青春期叛逆的因素,也可见其激情,无怪乎他后来列举编辑的职业素养,格外强调“激情”。二是他的带病下乡。李昕十四岁那年被协和、日坛、朝阳三家医院确诊患淋巴癌,存活期仅有四到六年,医嘱静养,“五年免体免劳”。如此病情,他居然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人干的农活他一样不落下,真是不管死活。神奇的是,八年后复查,肿瘤消失,癌症居然凭空消失了,可谓传奇。三是出于正义感和血性,为受害知青鸣不平,写公开信,因此得罪公社书记,致使原本板上钉钉的入党和上大学这一改变命运的“成双好事转头空”。这件事特别能看出他日后做书的胆识和担当。
有这样的前传作背景和铺垫,我们似乎更能理解李昕四十年的出版生涯这部正传。曹聚仁的回忆录名为《我与我的世界》,我觉得此书题可以作为概括所有自传或回忆录的模版。李昕的回忆性随笔,都是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亲历亲见的往事。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与作家学者打交道,书里书外,都是故事多多,借助写日记好习惯积累下的记录,加入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如此夹叙夹评的文体,既是回忆,又是随感,集合起来就构成了自成一片天地的“李昕与他的世界”。这里的“世界”,也可以换成“时代”,也许更贴切。这既是“李昕们”77、78级堪称辉煌的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的写照,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既辉煌又令人怀念的大时代的文化侧影。
赶上了出版的好时代
回首往事,李昕常说自己“生正逢时”,“赶上了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