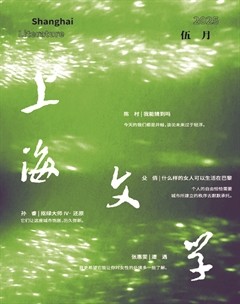“双叶丛书”之出版,乃属因缘际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界散文中兴,我作为一名文学编辑,自然也想赶“潮”,而我的作者队伍多为文坛前辈,有不少是夫妇作家,我油然陡生为他们伉俪编一本散文合集的想法。在书稿的内容上,我抓住家庭的特色,选他们写家庭、亲情、人生的随笔;在篇幅上夫妇各占一半,在文末用“编后记”将两人联系起来,使其成为珠联璧合的整体,体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趣味。同时,凡健在者,各自为其作品作序、题写书名,再配上家庭生活照或与内容相关的图片。在装帧形式上,美编速泰熙先生匠心独运,一改封面设计老套路,首创“一本书两个封面”,或曰“无封底无封面(即夫妇各自为政)。”后来出港台作家的书,先生部分用竖排,女士部分用横排。有人戏称这是“阴阳有别”“一国两制”,遂成了一本无所谓前后、无所谓主副的书。
最先出版的一辑,萧乾、吴祖光、黄苗子、冯亦代四对夫妇的人生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经过岁月的淘洗,屡遭“霜打”,初拟丛书名“霜叶”,后考虑丛书要扩大阵容,传主人生经历有异,用“霜叶”不妥,改用谐音“双叶”。
第一辑面世后,获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萧乾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称:“这种形式可谓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出版夫妇合集,体现男女平等的首例。”
继第一辑健在作家夫妇合集后,我们拓宽视野,兼收已故著名作家夫妇的作品,遂有后面陆续跟进的十二部。
在“双叶丛书”出版过程中,发生不少有趣的故事,显示传主们的操守与人品,现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萧乾:“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我之所以把萧乾先生列在介绍的首位,因为他对“双叶丛书”的出版鼓励有加,费心最多,支持最力。中国台湾的林海音、柏杨、美国的聂华苓、英国的陈小滢(陈源、凌叔华之女)以及梅志都是他介绍给我的。
一九九三年秋我着手策划这套丛书,曾写一信致萧乾,投石问路。萧乾接到信后即作复。他说一九九四年是他与文洁若结褵四十周年,用合译《尤利西斯》纪念,再加出版两人的散文合集,是锦上添花了。复信中还说:“你们这个点子想得极好。搞出版就得这么动脑筋。我全力支持一切严肃的、认真的、从民族文化出发的举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致笔者函),并告知已经请助手傅光明着手搜集文稿了。
春节后我进京专事拜访萧乾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工作室兼客厅仅十坪左右大吧,墙上挂着他与巴金、他与冰心的大幅合影。室内显得比较杂乱,书架上立着一排他自家的著作和他喜欢听的录音带,办公桌被一张大饭桌挤到靠墙的一隅,桌上摊着正在译的《尤利西斯》文稿和工具书。桌下旁边一只方凳上放着一溜药瓶子、剪刀、胶水。十分有趣的是室内交叉地拉着两条绳索,挂满来自世界各地五颜六色的贺年卡,活像一面面万国旗。更逗的是靠办公桌的一面墙的钉子上,挂着两个带铁夹的小本子,桌子腿下方钉子上拴着一本拍纸簿(中央文史馆小便笺),活像生产队的会计账本。他右手中指上缠着一块白胶布,大概是握笔过久而致。我向他汇报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想,他说这个点子好,谈到拟收人选时,萧乾说:“一定得把钱锺书、杨绛先生请进来。”我说那得请您帮忙。他说他们认识,但交情不深。片刻,他说你找舒展,舒展与钱先生有交情,刚帮他编六大本“论学文选”。我说我不认识舒展。他说我帮你介绍。说着从桌腿上拴着的拍纸簿上撕下一页给舒展写信,并把舒展的电话、地址一并抄给我。
告辞时我提出想合张影。萧乾坐上沙发招呼小保姆帮忙。拍照时我坚持站着,他说“那我也站着”,还真的立起身来。我说:“您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您是前辈,我是后生。”萧乾反对:“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我连说“不行不行”。他说:“那好,一样来一张,大家平等。”就这样几乎在同一瞬间,照了两张不同姿势的合影。一张两人平坐,一张他坐我站。
萧乾很快将书稿寄来,但没有给书命名,他说让我代劳。我知道萧乾是浪迹天涯未带地图的旅人,一生颠簸流离,有四段恋情,最后遇到文洁若始安定下来……我提议就叫《旅人的绿洲》,他很高兴,来函称这个书名“雅而恰当”。
《旅人的绿洲》出版后,我登门送样书,他十分满意,还专门签了一本送我,上书:“昌华同志,谢谢您的精心编辑。”后来又在报上写了篇《智慧与匠心——向出色的编辑致敬》,美言我一番。
萧乾先生古道热肠。尤令我感动的是《双佳楼梦影》(陈西滢、凌叔华辑)中,有一篇陈西滢写他与萧乾拜访福斯特的日记。原稿字迹潦草,文内夹着许多人名、地名、花草名,我无法编辑,请萧乾帮忙。八十六岁高龄的萧乾抱病为这篇日记作了二十七条注,满满三大页,还幽默地说我是在考他,他记忆力衰退难以考及格了。
萧乾对人的热情与忠厚我深有感触。傅光明当时是他的助手,萧乾十分赏识他。《旅人的绿洲》萧乾部分的文稿是请傅编的,他向我提议署名时署傅的名字,“如不宜,则我也加上,但事实上是他花的力气。”叮嘱我一定要给傅选编费,还提出方案:“1.由出版社付;2.由我们的稿费中扣除。”但希望直接寄他,“即便由我稿酬中扣,亦不要注上”。还念念不忘地在“不要注上”四字下面加着重号。(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致笔者函)
更令我铭感五内的是他对我的关怀与提携。我后来走上创作之路,写了十多本书,是与萧乾先生的教育开导分不开的。一次,他问我写不写文章,我说当教师时写,改行当编辑后,工作忙就不写了。他听了直摇手,说:“你要写,一定要写,只有你写了,才知道作家的甘苦。只有你有了作品,才能与作者平等对话,也容易沟通……”他还抱病为我的第一本书《书香人和》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他的序不是一味捧场,在鼓励的同时,指出书的软肋:“论人有余,品书不足。”
萧乾先生是根直肠子。某年我去访他,恰逢央视“电视书屋”剧组采访。他是搞书评研究出身,主持人希望他谈谈对时下文学评论的看法。萧乾说:“目前搞好书评有难度,社会风气不大适宜。本来一部书出版,应该有很多人出来说三道四,而现在我们的书评往往一边倒,全说好或全说坏,以偏概全。说好话(假话)的人多,说坏话(真话)的人少。”他还指出也有少数人用权或用钱来左右评论……最后,主持人请他说一句他最想说的话。他说:“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说这话时的神情,他用手做刀状横在脖子上做切割状说:“如说真话就这样,我不干。”还幽默地说:”我钦佩张志新,但不想做烈士。”后来应我之请,他把“尽量”这句话题赠于我。
我与萧乾真有缘分。二○一八年一个偶然,我在“孔网”上拍到萧府流出的文洁若先生的一本“杂记本”,在那个本子上我见到不少在公开出版物见不到的东西:如他为老舍代笔写稿分稿费的事;如巴金到京,曹禺请客他作陪并抢先付账的事。还有他自拟的墓志铭:
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是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文洁若先生十分谦逊、平易近人,当年她把《旅人的绿洲》她那部分文稿寄给我,我通读后,觉得有两篇可能是她出于某种考虑收在书中,不大妥,斗胆建议撤换。文先生十分大度,立即调整了篇幅。萧乾逝世二十多年了,我与文先生一直保持联系,为纪念萧乾百年华诞出书的事,我帮了点小忙。文先生说“萧乾没有白疼你”,这话真让我暖心。二○一八年我去拜访文洁若,告辞时她忽然说:“张昌华,慢走,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作纪念。”原来是她当年亲手为萧乾织的深蓝色毛线帽。二○二○年我去看望文先生时,她左手骨折,肿还没全消,还在伏案笔耕。一个勤奋一生、为祖国编译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人。
巴金:“可以。”
“双叶丛书”策划之初,我即将巴金先生列为领衔者。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读巴金的书长大的。他的为人为文,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三观”。可此前我与巴金及其亲属素无交往,遂请萧乾先生向巴老及其亲属转致我的请求。巴金觉得萧珊生前此类散文作品不多,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不出,遂通过小林十分委婉地拒绝了。一九九五年四月,文洁若来南京签售《尤利西斯》,我去招待所看她,送她一只花篮。文先生第二天大早要到上海,她舍不得把漂亮的花篮舍弃,于是带到上海,以我的名义送巴金,希望为组稿提供一点方便。然而,仍无果。
丛书第一辑问世后,以内容选材的独特和装帧形式的新颖,引起了各层面读者的兴趣,特别是博得圈内人士的好评。伴之而来的是读者的探询或质问:为什么不出巴金萧珊合集?显然,那是巴金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他的血泪之作《怀念萧珊》,打动了多少读者!巴金本人不大想出,萧乾、文洁若出马也没成功,我只能作罢了。但罢而不休。经验告诉我:任何一部好作品,绝非轻易而得;而既作为一名编辑,总应有所追求才好,不轻言放弃。于是,我在等待。
终于让我等着了,天赐我也。一九九七年借北京图书博览会之便,我去拜访舒乙先生。舒乙说要抓我的差,说中国作协为九十岁以上的老会员,每人量身定做一双北京百年老店内联升店出品的麂皮软底布鞋,巴金的那双存在他处,托我捎给巴金。我一听即很兴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正是晋见巴老、向他组稿的良机。我一口应承。当时巴老在杭州西湖汪庄疗养,我请舒乙给李小林写封信,为我组稿事多美言几句。舒乙当即写了。回宁次日,我带着鞋持着舒乙的信直奔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