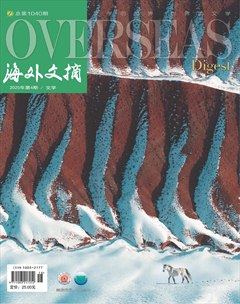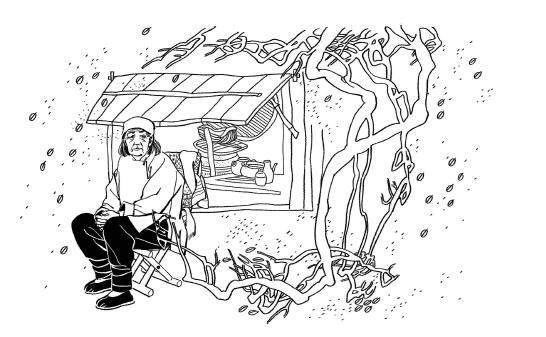
一
四十岁那年,第一次,我带着七十三岁的母亲去看望舅父。
我们乘坐的飞机从山东济南遥墙机场起飞,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到达武汉天河机场,然后乘坐出租车赶到武汉火车站,转乘了两个多小时火车到达荆门,又坐表兄弟租来的一辆一汽大众,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远远地看到一幢年代久远的宿舍楼下,并肩站着一对清瘦的老夫妇,那是我的舅父和舅母。
生活中,母亲很少说到她这个亲哥哥,只言片语中,我知道舅父自幼聪慧,外祖母大字不识一箩筐,把所有厚望都寄予了他,虽然身处农村,舅父却没干过一天农活,一心只读圣贤书,十七岁学业有成被国家分配到东北一个兵工厂工作,后来,工厂搬迁,又携家带口去了湖北。
兵工厂位于湖北荆门一处山坳里,四面环山,环境倒是幽静,只是闭塞偏远,人口稀疏(据说,当年很红火,如今早已没有一点红火的迹象),舅父住的房子是建于70 年代的老宿舍楼,两居室,不到六十平米;两个表兄和两个表姐都各自成家,就散住在舅父周围:“孩子们婚嫁的都是工厂里的子弟,所以都住得不远。”
不等我们搭话,舅父自顾又说:“厂子早就关停了,年轻人能出去的早都出去了,剩下的都是没出息的。”
两个表兄弟就很尴尬地讪笑起来,好在舅父话锋一转:“读书也不一定有出息,我从小就读书,走的这么远,又有什么好呢?孩子们都在身边不是更好嘛……”
母亲和舅母的笑容就很忧伤起来。
我们的到来,让舅父舅母开心得像个孩子,几天里,说不完的话。回程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坐上租来的轿车,摇下车窗,母亲抓着舅父的手说:“哥,我走了,你自己保重,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来看你……”
话音未说完,母亲就把车窗摇上了,因为她开始失声大哭。我站在车外,轮流去拥抱舅父和舅母,想说几句诸如“有机会也回家看看”之类的话,但是哽咽失声,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把舅父紧紧地在胸口抱了一抱——对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回家看看这种机会几乎不可能了。
在回荆门市里的山路上,母亲望着窗外绵延的群山,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那么小就离开家了,天南地北,老了也回不去……”
似在说给我听,也似乎是说给自己,泪水擦了流,流了擦,一直流到下车进入火车站,进入检票口,回身对表兄和表姐挥手告别,再次变为号啕大哭。
本来,那次去湖北,我还想当面质问舅父几件事:
1.为什么在外祖母有生之年不接她老人家到身边团聚小住?
2.为什么不回去给外祖母送终,让外祖母临终都没有看到让她骄傲的儿子。
但都没有说出口。
在我沿着窄窄的楼道,爬上舅父那位于四楼的房子后,就找到了答案:已经容纳了六口人的房间,是根本无法接纳外祖母的;山水阻隔,路途迢迢,外祖母是根本从山东到不了湖北的。
晚上,躺在舅父家狭窄拥挤的客厅的沙发上,朦朦胧胧听得一间卧室里舅父和舅母在窃窃私语,听不清说的是什么,等到睁开眼睛,想仔细倾听的时候,脑海里蓦然闪过一个念头:舅父不会在内心一直怨恨着外祖母吧?
是外祖母逼他读书识字,因此才远走他乡,才山水相隔。
外祖母晚年是不是想明白了呢?
舅父卧室的桌子上摆放着很多老照片,我看了一个遍,发现没有外祖母的照片,临上火车前,我把自己随身带的外祖母的一张一寸照片掏出来,递给二表姐,二表姐接过去,很好奇地端详着说:“这就是奶奶啊!”
二
五岁那年,我突发高烧不退,来不及找人帮忙,在漆黑的夜里,母亲和小脚的外祖母轮番抱着我,奔走十余里,赶到县第二人民医院,经医生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外祖母和母亲听罢涕泪滂沱,母亲一边哭,一边就开始张罗着找人去告知在一百多里外上班的父亲,外祖母却不让,母亲霎时翻脸,拽着外祖母的胳膊,就把外祖母往外拽,大嚷着:“你走吧,你回你家去吧,别管我家的事儿了!呜,呜呜!”
不久前,外祖母也阻拦过一次母亲。父亲的一个同学当了县人事局局长,有能力把母亲从乡下调到县城,母亲蠢蠢欲动,想带着我们举家搬迁,外祖母却极力反对,理由是母亲和我们的出现,会影响父亲的事业和生活:“男人要是整天想着家小,就不会有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