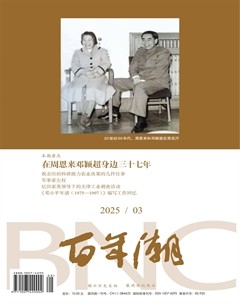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也在各国广泛开展。苏联、日本、德国、法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等国不但先后建立了左翼文艺组织,还产生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并且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领导下,建立了国家组织(先叫“无产阶级文学国际局”,后改名“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各国有它的支部。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以及相关作品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吸收无产阶级文学思想,提出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文艺的主张。与此同时,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政治话语权,也决定以革命文学作为抓手,鼓舞革命士气,发动广大民众,左翼文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调和论争,为“左联”成立奠定基础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是以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作为开端的。中共在这场论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始终秉承“求同存异”的方针调和革命文学内部的争端,为“左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创造社与太阳社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影响较大的激进文学团体,其成员也是“左联”成立初期的主要人员。创造社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留日学生1921年6月8日在东京创立的。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入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太阳社于1928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团体的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具有留苏背景的中共党员,均强调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1929年下半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东京支社,先后编辑《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刊物,并编辑出版“太阳社丛书”。
早在1923年,一批从事革命工作的早期共产党人,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沈泽民、李求实等,便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宣传下,“革命文学”口号逐渐被文艺工作者们吸收接受。创造社与太阳社二者虽然都是大革命失败后宣传“革命文学”的重要团体,但由于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分别师承日本与苏联,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以蒋光慈为代表的太阳社认为作家如果想成为时代的表现者,必须理解现代生活,即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蒋光慈提出的“文学反映论”遭到了创造社的强烈反对。1928年,成仿吾在《文化批判》上发表《打发他们去》一文,开始对蒋光慈等人展开批判,“这种工事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般地,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他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在文艺的分野,把一切麻醉我们的社会意识的迷药与赞扬我们的敌人的歌辞清查出来,给还它们的作家,打发他们一道去”。
创造社与太阳社二者之间的论争,引发了中共的密切关注。在中共的积极介入下,两社为促进彼此间的团结和进步,决定召开联席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28年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指出:“虽然不知‘太阳诸君’,对于我们如何,然而我们始终把‘太阳’认作自己的同志,所以‘太阳’有了好的作品,我们负有介绍的义务,而‘太阳’有了错误,我们是负有指摘的责任。”
至此,创造社与太阳社二者之间的论争逐渐结束。不过,这两个团体紧接着联合起来,开始批判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代表作家。
1927年,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他在文中将鲁迅、周作人、陈西滢等人认定为“趣味文学”的代表人物,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1928年,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提出要“就中国混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冯乃超在文中将鲁迅刻画成“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落伍者形象……他所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
除此之外,杜荃(郭沫若)也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提出他原以为鲁迅只是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鲁迅的态度是中间,不革命的,最起码鲁迅应该不是反革命,不过当其读了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后,他认为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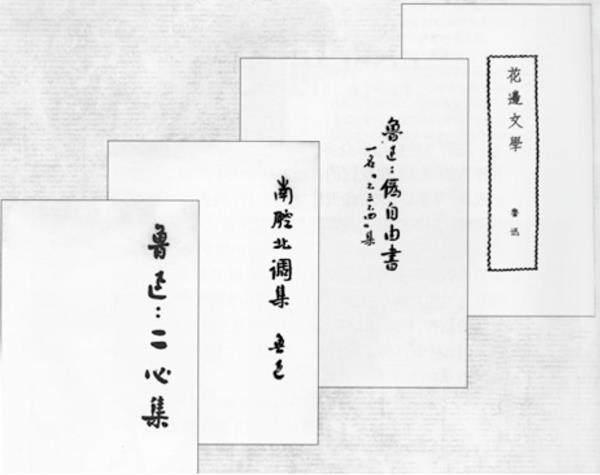
对鲁迅批判最激烈的要数太阳社的代表人物钱杏邨。1928年钱杏邨在《太阳月刊》上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在该文中对鲁迅进行全面批驳,认为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鲁迅创作时代“决不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仅仅“只能代表新民报业时代的思潮,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他认为鲁迅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以及所谓的自由思想害了他”;从当时中国农民的情形来看,“阿Q时代早已死去了”,中国农民“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同时中国农民“革命性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钱杏邨最后指出,“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
面对来自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们铺天盖地的批评,鲁迅逐一展开反击。他先后撰写《“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路》及《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等多篇文章同两社展开论战。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首先对当时革命者所提出的“革命斗争”以及“超时代”展开批驳,他认为,“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随后,鲁迅又发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批判当时革命者机械性照搬别国的行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