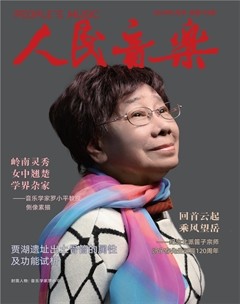在音乐和考古领域,张居中的名字始终与“贾湖骨笛”紧密相连。1986 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一支“穿孔骨管”,在他的手中从“无名器物”升华为改写人类音乐史的“贾湖骨笛”。这一发现不仅突破了学术界对史前艺术的认知边界,更用实证将中华文明的音乐基因追溯至九千年前。
作为贾湖遗址考古发掘的关键人物, 张居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鉴定这些文物,更因他致力于推动它们在学术领域不断被深入研究。从发现之初的惊鸿一瞥,到往来奔波的鉴定执着,以及跨越十余年的测音间隔, 张居中与贾湖骨笛结下了不解之缘。笔者深感荣幸,多次登门求教、深入访谈,更有缘一同实地考察,目睹了保存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贾湖遗址博物馆的骨笛原件。“由人到笛”进而“吹笛知人”,在张居中教授的手中,这小小骨笛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如何一举成为天下闻名、冠绝九千年音乐文物的呢? 笔者试图从多个维度, 勾勒出张居中教授与贾湖骨笛的这段不凡经历。
一、多学科交叉的科技考古研究
张居中的学术之路始于对黄土之下文明密码的痴迷。1978 年, 他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考古学家安金槐、李友谋、贾州杰等教授。大学期间通过登封王成岗、禹州瓦店等多处考古遗址的实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田野考古基本知识和技能,也第一次体会到地层学的精妙:每一铲土都可能是历史的切片, 错判一层, 便可能颠倒千年。这种对地层堆积的敬畏,成为他日后严谨治学的基石。1982 年, 张居中进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投身于中原史前文化的探索。
在张居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他不仅注重把科技运用于考古实践与研究,还注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以开拓性思维推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多维度融合。例如20 世纪80 年代末,他在主持贾湖遗址发掘过程中,尝试突破传统考古模式,组建了涵盖植物学、动物学、土壤学、声学等多领域专家的研究团队。在分析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作遗存时,他邀请古植物学家孔昭宸、农学家王象坤教授合作, 通过植硅体分析和大植物遗存分析技术,首次确认了淮河流域8000 年前人工栽培稻的存在,这一发现改写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认知。
1986 年,他与河南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合作,提取到中国最早的龋齿病例样本和人体颈椎小变异样本,为探讨新石器时代人类饮食结构演化和人体结构微演化提供了实物证据。1990 年,他与周昆叔教授合作对贾湖遗址进行微环境复原研究时,通过采集地层中的孢粉、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样本,结合地质沉积物分析和古气候模拟,重建了史前贾湖“湿地- 岗地”交错的生态景观,揭示了先民依水而居、渔猎与农耕并重的生存策略。这种将微观生态证据与宏观文化现象结合的视角,成为他研究史前社会的重要方法论。
在破解贾湖骨笛音乐功能的过程中, 他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专家,运用声学频谱分析技术, 证实这批距今约八千年的骨笛能够演奏六声音阶甚至七声音阶, 且具有良好的音响性能, 改写了学界对史前中国音乐文明的认知。正是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张居中通过建立“考古遗存- 实验分析- 理论构建”的研究链条, 开创了中原考古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典范模式。
二、贾湖骨笛的发现与鉴定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前期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 但直到1983 年才开始系统的考古发掘,迄今共进行了10 次。张居中参与了其中的多次发掘工作,并在第二至第六次发掘中担任田野考古工地主持人,第七、第八次发掘中担任考古发掘领队。
贾湖遗址的第一次试掘始于1983 年,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实施,郭天锁、陈嘉祥等主持,发掘目的是初步了解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情况和文化特征。1986 年,在第四次发掘中,M78 号墓中发现了两支骨管, 这是贾湖骨笛的首次发现。当时,他观察到骨管一侧排列着7 个小圆孔,但因缺少吹孔和箫的山口等特征, 无法确定其是否为乐器,于是暂记为“穿孔骨管”。
为了鉴定这些骨管是否为乐器,1986 年8 月,张居中在李京华、赵世纲先生引荐下,带着M78 号墓的两支骨管及M121 号墓出土的一支碎骨管,前往郑州国际饭店请教参加纪念朱载堉诞辰450 周年国际会议的专家,希望借助音乐专家的力量解开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