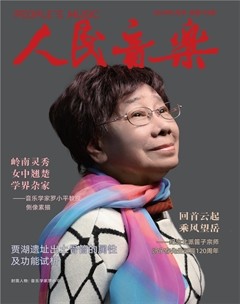2024年7月20日,由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委约武汉音乐学院龚华华教授创作的《中国第一交响乐:楚魂》,于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年度音乐季闭幕音乐会上演。静心聆听之,无不被其中那些历史文化的声韵、细腻精当的技法、浓淡相宜的音响等特质所吸引。这部交响乐由“筚路蓝缕”“巫歌祀舞”“章华长袖”和“奋翅而飞”四个乐章构成,在时长近五十分钟的宏大叙事中,作曲家运用不同流俗的体裁模式与形式语言,为我们唤起那古楚国遥远历史的文化记忆……
一、第一中国交响乐?!
以“第一中国交响乐”——这种被特别强调的体裁而名之,使《楚魂》既彰显出创作者对国乐形式的执持自信与革新勇气,又在立意层面上表现出这部作品创作的特殊追求与拓新意涵。显然,选择交响音乐这一器乐类型,就已在规模、难度等形式要素方面为创作设定了很高准绳,再加上“中国”与“第一”这两个“抢眼的”定义,便让这部楚文化题材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形象及寓意内涵上赋予某种“国家意义”。
因此,当人们在聆听这部作品时,不禁会有疑问:“第一中国交响乐”这一体裁形式从何而来,作曲家通过这一命名又寄托了何种表达诉求。从来源上看,“中国交响乐”这一体裁,最初是由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提出的,也有多部新作运用这一体裁,对中国民乐进行有成效的探索。从“民族管弦乐”到“中国交响乐”,尽管这两个概念因产生的时空语境和意义内涵等范畴不尽相同,却都关乎中国文化传统的守正创新与当代音乐创作的拓新发展,也都因关乎中国音乐创作的过去、当代和未来而具有时代价值。站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看这一概念,其中至少表达了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向度,即当代艺术家们在面对中西音乐文化交汇时,对本土文化立场的自觉体认与基于全球视野对艺术理念创新的一种探索精神。
一提到交响曲,人们往往会将其生成历史与创作实践等内涵投射到西方。但实际上,从形式角度来说,同样都是大型管弦乐队,中国交响乐运用的是民族管弦乐队来讲述中国故事,在中国传统音乐这一庞大的话语体系中,传统乐律、调式体系、传统结构、音腔旋法、线性思维、句法形态、多声混合织体、支声复调等作为中国音乐创作历史发展中的特性语言,亦是当今国乐话语富于文化精神的力量之源。可以说,中西方交响乐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巍然屹立,而“中国交响乐”的提法无疑是把两个强大的传统音乐话语体系置于当代语境的对话之中,使之成为展现中国传统与艺术审美的形式载体,但又运用现代性交响语言赋予国乐新的音响意义。
龚华华在面对这一体裁时,主动尝试突破中国民族管弦乐写作的思维惯式,基于他对楚地文化与创作立意的深度思考,借助于现代作曲技法,将不绝如缕的绵绵楚音巧妙安排于音乐始终,通过提炼传统的鄢郢音韵来探寻本土音乐语言管弦化与交响化的拓新表达方式。一方面,将创作内容内化为一个个修辞元素并通过富有逻辑的结构布局方式与标题叙述达成契合;另一方面,依靠作曲家扎实深厚的荆楚传统音乐功底和作曲技术功底而与其“楚人” 的身份相加持, 更让这部作品具备独特的文化视角与音乐叙事方式,更好地向听众展现出一份曾几何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古楚国记忆。
二、煌煌楚史八百年,绵绵不绝入题来
上数三千年, 一个创造过辉煌历史的楚国,今天的人们却知之甚少。自立国到公元前223 年灭国,楚国历经四十余代君王,可以说楚人一直在为重回中原、称霸中国乃至一统华夏的目标努力。从楚武王熊通年逾七十征讨随国,到“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将武力与礼仪合二为一,使楚国逐渐强大至问鼎中原;再到楚灵王、楚怀王疏远屈原终致国力衰微……在写不尽的八百年楚国历史与文明底蕴面前,作曲家又该如何“选择”?
龚华华的“楚之国”始于“筚路蓝缕”。窥其写作用意,似与楚国先君若敖、蚡冒开创基业而开荒辟地时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相关。尽管在全盛时期的楚国幅员辽阔, 但其立国之初可谓经过数百年饱尝艰难与奋斗的历程后, 才最终得到中原王朝承认并完成建国。作曲家为了营造开国之初的鸿蒙声景,乐章伊始,便以“a-e-g-b-a-e-g-#f”的核心音调发声于大提琴与低音提琴弱奏之下,随即便在逐层叠加中通过对这一核心动机的碎片化处理,并运用泛五声性调式语言为全曲声效做出色彩铺垫。在引入完成后,核心材料以连音的装饰奏法,不绝如缕地由拉弦乐器组作为前景音响持续呈现,让音乐整体在“慢-快-慢”的速度变化之中,既始终贯穿了核心音调,又让人在听觉上无困乏之感。作曲家在该乐章让节拍不断地交替变化,使绵绵楚音时而流动低吟,时而合纵高亢,音色音响过程处在由淡而浓再归于清宁的造型之中,借助调式泛化、和声游移、织体对位等形式让乐思在丰富而细致的技术手段中自如展衍,将楚人一路走出蛮荒荆棘、健履阔步、发展壮大的恢弘历史,熔铸于现代乐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