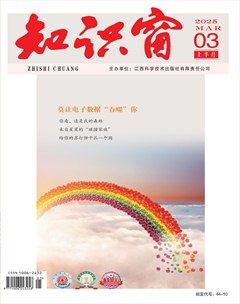石钟山为什么叫石钟山,为了探究这一命名,演绎了一段漫长的探究真理的佳话。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石钟山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对这个说法,有人持怀疑态度,其理由是: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有大风大浪也不能让它们发出钟鸣之声,更何况是石头呢?
对于郦道元的结论,唐朝的李渤并不信服,于是他前往石钟山,发现两块奇特的石头。当地人称这两块石头叫“石钟”,被敲击后能发出铿锵声响。李渤敲击两块石头,声音果然奇异。至此,李渤认为石钟山就是因这种名叫“石钟”的石头而得名的,并写下《辨石钟山记》。
但是,李渤得出的这个结论同样没能说服苏轼。苏轼认为,被敲击后能发出铿锵声响的石头到处都是,可唯独这两块石头被叫作“石钟”,是为什么呢?
后来,求证的机会来了。苏轼父子顺路经过石钟山,便连夜乘船来到了石钟山下。小船夜里在悬崖绝壁处停泊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所幸苏轼颇有收获:石钟山下都是石穴和缝隙,不知它们有多深,细微的水波涌进里面,水波激荡,发出洪亮的钟鼓之声;有块大石头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孔洞,把清风水波吞进去又吐出来,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就像音乐演奏。
基于此,苏轼得出了在他看来非常合理的结论:眼见为实,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说法没错,但是描述得太过简单,没有讲出其中的原理,而李渤的“敲石头论”就是胡说八道。苏轼满意而归,写下了《石钟山记》,肯定了郦道元认为石钟山因“声”得名的结论。
然而,明清时期,不少人认为苏轼关于石钟山因“声”得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石钟山应该是因“形”得名:山形似钟,故以钟形命山名。
还有人认为,主声派与主形派都有一定的道理,应将两者综合起来考察。例如,清朝郭庆蕃在《舟中望石钟山》一诗中阐明自己的看法:“洪钟旧待洪钟铸,不及兹山造化功;风入水中波激荡,声穿江上石玲珑。”
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就应了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无独有偶,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对中国地理著作《禹贡》中“长江源于岷山”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禹贡》中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为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意思是长江源于岷山,向东分出的支流称沱江,长江向东流到澧水,流过九江,到达东陵,再向东偏北到彭蠡泽,彭蠡泽以东称中江,最后流入东海。
一直以来,《禹贡》中“岷山导江”已经成为定论,被广泛接受。但徐霞客“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经过实地考察,他发现金沙江比岷江长得多,所以他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源,并在《溯江纪源》中写道:“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谿峒间,水陆俱莫能溯。”
在这里,徐霞客拿渭河只是黄河的支流而非源头进行类比,他认为,岷江也是长江的支流。他还分析了人们误认长江源于岷山的原因:岷江可以通航,而金沙江不能通航,且金沙江多流经高原深谷间,人烟稀少。
现在我们都知道,长江的上源不是金沙江,它发源于格拉丹东。于是有人认为徐霞客在这方面的探究没有价值——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徐霞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其实不然。
探究任何事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禹贡》中的说法是“岷山导江”,徐霞客怀疑这个说法,并且历尽艰辛进行实地考察,推翻了《禹贡》的说法,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到了近代,又有地理学家怀疑徐霞客的说法,于是他们跋山涉水,走上了考察长江源头的征程。后来地理学家证明,徐霞客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长江的真正源头在格拉丹东。然而,我们要知道,真正确定长江这个源头,是1978年的事情。而徐霞客已经去世337年了。也就是说,在徐霞客的时代,格拉丹东一带荒无人烟,他几乎不可能到达那里。时代成就了徐霞客,同时又限制了徐霞客。但徐霞客探究的意义在于,他不迷信前人,推翻了一种错误的结论,尽管他的结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为探究长江的源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探究长江源头的历史前进了一大步:我们离错误越来越远,离真理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说,探究真理是一场接力赛,一场有起点却无终点的接力赛。这个过程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每一次大胆的怀疑和随之而来的认真而严谨的证明过程(即使他们本身的说法不对)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