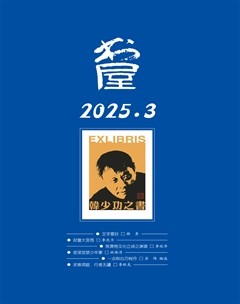清宣统元年(1909)九月一日,王闿运在《曾文正公日记序》中写道:“惜其记事简略,非同时人莫能知其涯涘。故闿运观之而了然,不然喻之人也。时历四纪,欲学裴松之以注辅志,则记录文字不备,无从搜求证明,此轮扁所以叹糟粕与?”
笔者这本小书,就是受到王闿运这段话的启发,试图在某一方面把他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做出来。之所以说某一方面,是因为笔者试图做的,与王闿运打算做的,并不完全相同。王闿运打算学裴松之注《三国志》,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和“有所论辩”,来弥补曾氏日记记载之不足,工程可谓浩大。笔者则是将曾国藩奏稿、批牍、诗文、日记、书信等文字背后的隐情,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写成系列小文章,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不仅能够增进对曾氏文字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可以发现和认识一个不一样的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力争比较准确和完整地再现湘军的历史,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希望读者朋友读过此书之后,能够真切感受到:曾国藩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是科举时代靠读书和考试改变命运的人。他不是“圣人”和“完人”,而是一个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既不平凡又十分普通的人,与同时代其他学而优则仕的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刻苦努力,又高度自律,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最后才能够成就自己。
在曾国藩留下的文字背后,被他有意隐藏起来的故事和故意避而不写的内容,不仅非常多,而且相当有意思。在此不妨试举数例,请读者朋友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十七日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傍夕接次青信三件、南屏信一件,必欲余派吴退庵带勇三千。夜,头闷颇甚。”
刚当上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急于扩充兵力,却苦于找不到好的带兵统领。好友李元度和吴敏树极力推荐吴士迈,说他可做三千人统领。此举按理说求之不得,然而抹不开情面的曾国藩,虽然硬着头皮答应了,事后却深感头痛,其中故事是不是值得深入挖掘?
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一日寅时初刻,与曾国藩做了十九个月夫妻的陈氏妾,在安庆两江总督官署去世,年仅二十四岁。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没有就没有了,她的家人该是多么伤心和难过!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居然听不得陈氏母的哭丧声,并在当天日记中毫不避嫌地写下:“是日内室后事皆陈氏之母与兄嫂为之。申刻大敛。竟日闻其母号泣之声,心绪殊劣。”
对于陈氏母(应该称之为曾氏岳母才对)的哀伤和哭嚎,曾国藩为何如此反感和厌恶?在这句极其反常的话语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初一日日记中,曾国藩则写道:“巳初(上午九时许)出城,至上新河观新设木厘局(木材税务稽查机构),司道、府县皆至,小坐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