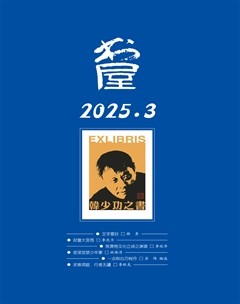温海明教授的大著《论语明意》即将付梓,承其美意,命我为序,坚辞不获,不得不勉为其难,聊叙拜读之心得如下。
先说作者学术之宗旨,或可曰“道意之辨”。
众所周知,“道”作为一哲学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位极荣宠,“莫之与京”。不仅儒、道、佛三教之精义,须赖此一“道”字以光以明,而且诸子百家之思想,亦莫不借此一“道”字以大以彰。“道”之为物,与西方文化之“逻各斯”和印度文化之“梵”差可仿佛,三者皆具本源性、语言性、规律性等内涵。至于儒、道、佛三家义理之所本,则又有分判:儒家以“仁”为本,道家以“无”为本,佛家以“空”为本,亦可谓各有宗旨,衢路分明。历来欲会通三教之大德硕儒,多以“中”字弥缝三教,曰中道、曰中庸、曰中观,庶可舍筏登岸,殊途同归。
反观儒学内部,向有理本、气本、性本、心本等多种本体论言说,晚近又有学者提出“情本”“仁本”之论,虽胜场各擅,亦莫衷一是。本谓此中胜义已尽,不意近年温海明异军突起,于“道”之外,特拈出一个“意”字,创为“意本论”之新说,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揆其理路,盖以“道”“意”之间,原本不二,经典所载之“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须由诉诸“言”而又不执着于“言”之“意”来疏通和解会。故“道”不唯离不开“意”,甚至“意”亦可成为一本体性概念,有着超越“情本论”“理本论”的哲学阐释价值,此即所谓“意本论”哲学。
“意”作为一哲学范畴,是否能上升到与“道”同参的本体论高度,或许还可商榷,但海明兄在“言意之辨”外,又提出一“道意之辨”,其问题意识极为敏锐,理论勇气亦足可敬佩。须知“言意之辨”,乃儒、道两家共同“话头”,如《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又《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凡此种种,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然而,正如王弼在“言”“意”之间,插入一个“象”字,称“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遂使“言意之辨”更趋精密和完备一样,海明兄此番“寄言出意”,将本属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的“意”,从“形下之器”向上拔高一层,使与“形上之道”遥契互参,甚至等量齐观,从而在“义理学的诠释学”层面,赋予“意”以近乎本体论的诠释学功能——此一番用心良苦的“理论经营”,对于中国哲学的本位话语转换和本土理论建构,或真能收“嘘枯吹生”“夺胎换骨”之效,亦未可知也。
次说作者撰述之特色,或可曰“明意之辨”。
温海明是我同辈学者中,具有打通三教、融汇中西之强烈问题意识和学术抱负者。多年来,他以“著论”和“注经”相结合的方式,苦心孤诣,盈科后进,步步为营,陆续写出《周易明意:周易哲学新探》(以下简称《周易明意》)、《道德经明意》、《坛经明意》、《新古本周易参同契明意》等四部大书,加上这部数十万言的《论语明意》,庶几完成了其“意本论哲学”的体系建构。其学出入中西,调和古今,会通三教,虽立足比较哲学之视野,而不失中国文化之本位与殊趣,故颇能开新而返本,辨异而玄同。
所谓“明意之辨”,盖指人名与书名之辨。温海明本是作者姓名,然其取一“明”字以为学,遂使“声色大开”,境界全出。其在《周易明意·后记》中云:“从入哲学门始,就发心要明白解读《周易》,并依托卦爻辞建构一个哲学思想系统。”据此可知,其早期“明解”之谓,既秉承“明白解经”之初心,亦含“海明解经”之隐语,机带双敲,一语双关,不无“姓名学”之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