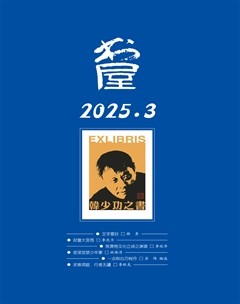“我们是念旧的一代”
周围嘈杂的声音像海潮一样退去,一只灰喜鹊隔着玻璃大窗寂然地飞走了。有人说过,雨天是读书天。我已经在海边一家酒店的“SEE SEA”咖啡吧,读写了一段时间。秋雨是寂寞的,书籍比秋雨寂寞上百倍。今日读的是《行走的书话》(沈胜衣著,海豚出版社2017年版)。
沈兄在自序中引述自己在《行旅花木》扉页上给朋友的题词:“人生亦一场漫漫行旅,且觅些花木沿路相随。”《行旅花木》是接下来我要阅读的,一向下笔干脆利落的我,笔下的文字竟然像是被雨水打湿了,湿答答的。
沈兄往返香港,深有感触:“我们亦无非以书店为床榻,以书卷为被铺,既对接也隔离时代的惊涛骇浪。”二十五年前,我旅游自美途经香港回到内地。“文学,为这座城市引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书籍,样样都精美。沈兄是香港大小书店的常客,“每回逛香港书店,皆觉满目春色,几乎要揽个满怀”。沈兄夸赞港版书籍:“装帧非常漂亮,楚楚动人,风格兼容了民国的简洁大方与香港的清丽唯美,犹如繁华千树。”
《好书太多,时间太少》是美国作家莎拉·尼尔逊的书,一位爱书人的真情告白。是啊,有时候我们足迹不能到达的地方,他人花费心力替我们走了。我忽然想起吕大年的《替人读书》,不禁莞尔。正是因为读了《行走的书话》,我才这样说。我读得越仔细、越认真,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各色书店就“春色满怀”地与我相遇。譬如香港的榆林书店就在售卖沈兄的《书房花木》,看到自己的书摆在香港的书架上,沈兄偷偷地欢喜,虚荣心得到满足,为什么不呢?沈兄在坊间有“书店杀手”之称,寻书而来,书店却关门大吉。于是乎,“第三天,依然秋雨绵绵的早上,宅在酒店房间翻书——年纪大了,心境老淡,不愿多跑多逛,这样悠悠地消磨时间也挺好”。
来到台北,当然要去诚品书店。即使没到过台北的读书人也熟知其鼎鼎大名。沈兄“提着刚买的书,坐在书店门口抽两根烟歇歇脚,听着旁边卖唱乐队的歌声,看着这些地摊的场景,以及安静的街灯下奔流的车灯,茂盛的行道树上面白云涌动的夜空,那一刻,几乎有了点在巴黎的愉悦舒爽味道”,这些闲言碎语,像呼吸一样,盘活整篇文字。台南是台湾最古老的城,著名的茉莉二手书店,“既文化又家常”。街巷的古今书廊,也适合“打书钉”。即便一无所获,也无所谓。但一路走下来,往往总是这样:遇上,可意,犹豫,错过,追忆,遗憾。逛书店不留遗憾,不算真正逛过书店。只有遗憾,才激发心里的痛,不得与不可得,谓之“书缘”。前缘未定,后缘如何?“五月的台湾,且晴且雨。晴看乡野,雨访书店”,且晴且雨,典型的诗境之风。晴耕雨读书院编印的《开一间小书店》,记录一个女子在乡间郊野开书店的经历,书就放在门口,也是寄售品,却无人看管。我曾在日本的街巷见到人们丢失的东西,被放在物品丢失处,有衣服,还有贵重的项链等。民风非一日能养成,破坏却是一朝一夕的事。沈兄说到台湾作家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因为书名的原因,当年也淘购了一册,但没有阅读,因此对台南的凤凰花没有认识。沈兄因为此花重逢萧丽红的《桃花与正果》,遂买下来,存一份书缘。沈兄没有到花莲去,我想知道台湾的小说家王祯和与张爱玲的因缘故事,留一份残缺,可能就是下一次出发的理由。
在东京,沈兄留下的文字只一篇《东京,神田旧书街的雨》。怎么到处都是雨?我所在的咖啡厅的外面雨也在唰唰地落下,想象沈兄可能是一位极浪漫的人。古时候晒书的日子,是六月初六吗?好像林文月说过,曝书的日子是三月初三。不知道哪个更准确一些。古人把线装书一摞一摞地拿到室外,平铺开来,曝晒之,想想就是一件雅事。像神田旧书街,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近三百间新旧书店,书籍堆得满坑满谷,这样宽阔、热闹的书街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条。
终于到了伦敦,因为查令十字街84号,读书人的目光被吸引到这里。《伦敦,书影憧憧的街与巷》是沈兄《行走的书话》中最为深情的文章,写透了查令十字街的前世今生,原来其中还藏着王室凄美的爱情故事。但真正吸引人前来的,还是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芙这个名字被牢牢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