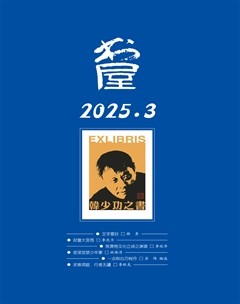一
年轻的时候,无论是在台北或是新竹街头,常会看到有一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可能断手,也可能瘸腿的乞丐,他们或坐或站,伸手向来往的行人乞讨。我是心存怜悯的,但通常不太会施舍;尤其是后来看到一些正常人假扮成残疾人,每天开着奔驰上下班,一个月可以乞讨到高达几十万元的新闻后,更是夷然不顾,悭吝不予了。
近几年来,台北街头已很少看到乞丐了,虽曾遇到过一些无业游民,他们也不会伸手跟人要钱。倒是常看到一些坐在轮椅上的残疾朋友,会在街角贩售刮刮乐、口香糖、纸巾之类的,在物伤其类的心态下,我有时候就会掏钱购买。也许,这十几年来,由于查核甚严,假冒不易,而且伪冒频传,人们已有戒心,“生意”也不怎么好做,所以渐渐销声匿迹了;也或许人们已经颇为富裕,不必再做这行营生了。的确,过去经常可见的乞丐,如今已经明显减少了。
如果人民生活富裕的话,想来一般人也不愿意沿街行乞、惹人嫌厌,毕竟乞丐一流总是让人瞧不起的。但我曾看过北宋人郑侠所画的《流民图》,时难年荒,衣食无着,再加上家园破碎,不沿路乞讨,又何以为生?看着那一个个衣不蔽体、瘦弱不成人形的乞丐,一面是怜惜,一面也庆幸自己生于现代。否则的话,以我的条件,恐怕不想当乞丐都很难了。
乞丐通常是身体有缺陷的,在古代,这样的人不太可能出头。武侠小说里常出现的“丐帮”,是由全天下的乞丐会聚而成的,金庸给他们冠上“忠义”的名号,俨然具有左右江湖大势的威望。这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宋代虽有个别小区域的乞丐组织,更有类似首脑的“团头”,但社会地位的卑下,让他们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更遑论社会影响力。古典话本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不正是因为嫌弃金玉奴出身乞丐之家,所以才狠下心将她推入江中的吗?我没当过乞丐,虽然可以差相仿佛地体会到乞丐看人脸色、逢人低首的窘状,毕竟未有实际经验,很难凭空揣想;但我却真的有被人当成乞丐施舍的经验。
一次跟团到山东参加《水浒传》学术讨论会,会议开完,照例是要旅游一番的,既是与《水浒传》有关,著名的梁山泊,我自是非去不可的了。
梁山如今已是无泊了,却成了重要的观光景点,入山口还特地砌造了象征一百零八条好汉的一百零八个阶梯,得先爬过这层层阶梯,方能当得成好汉。这当然非我体力所能及,所以我虽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却是被身强力壮的同行伙伴“背上梁山”的。过完阶梯,还要走很长的一段崎岖山路,才能抵达“忠义堂”。这时我是骑马,应该说是被马夫牵上山的。一路当然是颠簸难行的,到达终点时,我已满头大汗,不得不在路旁的一块大石上稍作歇息。
这时候,有几个登山客从身旁走过,一个慈眉善目的妇人看到我,竟然就从兜里掏出了两张一元的人民币,硬是要塞给我。我当然是连忙婉拒了。就在相持不下的时候,那个促狭的陈廖安,竟拿起相机,拼命地“咔嚓咔嚓”起来。好不容易请走了这位大姐,陈廖安居然脱下帽子,放在我面前,里面还放了一张十元的钞票,闪在一旁准备拍照为证。回到台湾,他在课堂上可是极尽戏谑地讲给同学听。我揽镜自照,左看右看,竟也发觉我真的是生着一张乞丐脸的,而且天生残疾,连假装都不必。心里在想,如果那位大姐塞的是两张百元钞票,我是收还不收?
这个疑惑盘绕在我心里很久,却又意外地获得了解答。一次去澳门,也照例去小试手气。当时我已玩得毫无兴味了,可同伴还在拼搏。我闲来没事,便拄着拐杖四处游观。不料有个妇人呼叫我,招手要我过去。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免就走过去相询。没料到,她居然翻开皮包,里面是一大沓黄色的千元港币,随手抽了一张就塞给我。我是既受宠又受惊,既疑惑又羞愧,莫非我真的就这么像乞丐?我没有犹豫,也不敢犹豫,连忙拒绝,快步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