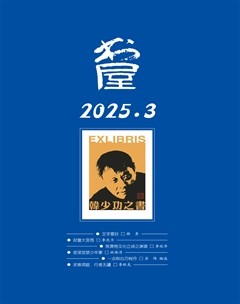能在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从思想、精神、性情、文风上都对鲁迅有着重大影响的绍兴人,是嵇康与徐渭,尤其是嵇康。
徐渭(字文长)与鲁迅,是两个南腔北调人。
绍兴市越城区坐落着徐与鲁的故居,一个在前观巷大乘弄十号,一个在东昌坊新台门(现在的鲁迅中路)。两个特立独行的巨人,为我们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丰富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有两首诗,曾让我有过他们一直同行的错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葡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自嘲》)
关于徐渭,在鲁迅日记中多有出现,涉及《徐青藤水墨画卷》《徐青藤水墨花卉卷》《徐文长故事》等。1933年3月7日这一天,鲁迅写下两篇杂文:《从幽默到正经》与《从讽刺到幽默》。前一篇直接提到了徐文长,“‘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这段话一直被误解,以为是在轻视徐文长,其实正好相反,是在为徐文长打抱不平。那时,戴季陶等人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反对“鲁迅们”的批判性杂文,甚至连“林语堂们”的“幽默”也不放过。鲁迅当然是揭露他们“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捎带着也为徐文长长期被世俗化的“堕于‘说笑话’”而鸣不平。《从讽刺到幽默》更深化了这些观点,直言想不要讽刺,先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并再次对幽默的现状与未来语中肯綮,且暗喻着徐文长被庸俗化成“说笑话”和“讨便宜”的悲哀:“‘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鲁迅当然知道徐渭的价值是在“说笑话”“讨便宜”之外的地方。徐渭的“青藤书屋”当是少年鲁迅常去的地方,那方小小的天井、天井中徐渭亲手植下的青藤,尤其是《青藤书屋图》两旁、徐渭手书的那副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更会让鲁迅凝望覃思的吧?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杂文集之名,怎会与“一个南腔北调人”不无关系呢?他在《〈南腔北调〉·题记》里说到一个上海女作家说他“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这是中国两个南腔北调人的相遇与相知。
与对待徐渭不同,鲁迅对嵇康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喜爱与疼惜,在灵魂的天空里,他们是一对双子星。
在《鲁迅全集》的众多版本里,我最先拥有与通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这套书其实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再版,它的第九卷由两部作品组成,一部是《中国小说史略》,另一部是鲁迅辑校编誊的《嵇康集》。
这部《嵇康集》,在鲁迅搜集整理的诸多古籍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陆续校勘的时间最长——自1913年至1935年,长达二十三年,几乎跨越了他整个的文学创作生涯;而且所耗精力最巨,前后校勘十余次,包括亲笔校勘本五种,抄本三种,以及《〈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和为《嵇康集》所作的序跋等堪称浩繁的手稿。我从先生的日记中择出几条,以记其大多在夜间进行的耗费心力的劳作:开始于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主要工程竣工时的1924年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10日“夜撰校正《嵇康集》序”,《序》的结尾是“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让其流传之意拳拳;1926年11月14日,写出四千字长文《〈嵇康集〉考》,“尝写得明吴匏庵丛书堂本《嵇康集》,颇胜众本,深惧湮昧,因稍加校雠,并考其历来卷数名称之异同及逸文然否,以备省览云”,深恐嵇康人与文湮没之心让人动容;1931年11月13日,“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直至1935年11月20日给台静农的信,又见校对《嵇康集》的信息,“校嵇康集亦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