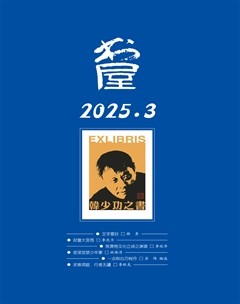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自幼读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华夏正统观已然培植。陈宝箴作为曾幕干才,早年在北京应举期间,恰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于酒楼酩酊远望,一时悲愤填胸,拍桌呼号,表现出刚烈血气。对外敌入侵之愤怒及对民族文化之眷顾,统合成当时士人的基本精神状态,也成为陈宝箴、陈三立两代青年的行为基准。此后在湖南巡抚任上,陈宝箴将维新改良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且有条不紊,不仅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起到明显作用,也对陈氏一门的性情家风产生长久影响。陈宝箴主持湖南“新政”,想走的是一条稳健改良的路子。他赞同郭嵩焘这样对西方国家社会有切实考察了解者的认识,也钦佩张之洞在处理洋务、开办近代企业及社会治理诸方面的切实成就,希望与他们携手,开辟中国的革新事业。他在引荐杨锐、刘光第,起用梁启超,为改良事业发挥重要影响之际,对于躁急冒进的康有为则抱有警惕。陈宝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因为“六君子”事件被撤职“永不叙用”,不仅自己饮恨以殁,更直接影响到子弟前途。其子陈三立只能以倜傥公子、落魄诗人身份彷徨一生,甚至也影响到陈寅恪一生学行。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社会的改造轨迹骤然向激进主义乃至社会革命方向转化,而在湖南新政期间为父亲颇多赞画的陈三立,思想并未趋于激进。对于日益蔓延中土的西方议会民主思想及制度,他亦抱抵制态度。在《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一文中,他袒露自己的基本社会观念:“余尝观泰西民权之制,创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论者或传其溢言,痛拒极诋,比之逆叛,诚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谓决可骤行而无后灾余患,亦谁复信之?彼其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然顷者吾畿辅之变,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騃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而以朝廷垂拱之明圣亦且熟视而无如何,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弊,盖天人相因,穷无复之大势,备于此矣。”简而言之,陈三立既不同意完全否定西方以民权为基本价值的社会制度,而对在中国实行此制度也不以为然。他认为,戊戌变法及义和团之乱均因为个别大僚之“恣行胸臆”,为朝廷用人不当。而秉承中国社会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礼仪规范,一个承继华夏传统又不逊泰西的理想社会,本来有可能在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权衡计较中实现。这也是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所揭橥的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陈三立又在为其父所撰“行状”中说:“故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旧党之见。……康有为之初召对也,即疏言其短长所在,推其疵弊,请毁其所著书《孔子改制考》。四章京之初直军机亦然,曾疏言变法事至重,四章京虽有异才,要资望轻而视事易,为论荐张公之洞总大政、备顾问。”
陈寅恪自幼游学外邦多年,并未追随一个长久的老师,阅览典籍无数,也未有一个恒定的楷模,但其祖、父的事业学行,却影响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