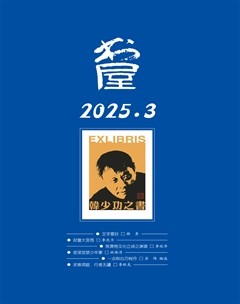一
韩秀,是一个写信的人。我也是。彼此通信的前提是,双方都有话说。通信从未断过则意味着,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回想2012年3月底,正期待在华盛顿将临的最美时节赴美,与韩秀相聚,当面呈上因她缘起的那本对我有着非凡意义的小书《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即收到她来信,言及现代人把纸质信件改为电子邮件,严格说来不能再叫“书信”。这对于老派、有古典情怀的人来说,读信的感觉相差太多。故而,时下仍有痴迷的爱信者,专门制作好看的信笺,且用毛笔写字。
凡事有两面性,电子邮件提高效率的同时,却失去了“家书抵万金”那种承载亲人生命的感情浓度和价值意义。在此,我是幸运的,除了电邮,不时收到韩秀写在好看的信卡和信笺上的文字,有的信卡是她特意定制的,颇为珍贵。她不愿用明信片写信,因为这可能会招致太多不请自来的读者。信卡有信封包裹,总算有“护甲”在身。一次,她寄来的信卡上,图案是一只黄色的猫头鹰安详地立在树枝上,绿的树叶,还点缀着一颗或两颗一簇、三颗一簇的红浆果。她在信里得意地说:“这信封,竟是毛边封口,颇具古意,我喜欢。”在信尾的“又及二”还特别注明:“Owl(猫头鹰),是我的收藏,极少送人。”
她书写的汉字俊朗秀逸,与之相较,我写出的竟是局促得舒展不开的“狗爬体”,不提也罢。结识十二年来,读她的信,不仅能在宁静中获得温暖,更能在思索中获得一种坚韧的力量。我打心底对她充满感激。
启程之前,收到她题为“复活节快乐”的信卡。她说:“我把清阁先生的信(原件)都保存在你的信夹里。改天,你来华府,便可将这些信件带回去,留作纪念。……清阁是位爱国者,跟舒先生一样。他们不是不能远走高飞,他们选择了留下,虽然非常痛苦。所以,我总觉得,清阁姨的信件是应当留在那块土地上的。从前,我没有人可以托付,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你,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我会将这些信件整理好,放在一个大信封里,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带回去了。你是一位研究者,手中的资料是原件更有说服力。”
我瞬间感到语言的无力,这远非什么感谢、感动、感激一类现成语汇所能表达。这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的话,要是上天让他能把心里所想用语言完美地表达出来,该多好(记得大意如此)。
与韩秀通信,话题极广,我想主要因为我们都算得上踏实写作之人,知道写作须勤且苦,能静下来不断自我充实。也因此,通信本身便充盈着一种鲜活的真而暖的力量。
4月10日,抵达华盛顿,5月1日返京。除了这次见面,我们都生活在对方的书信世界里。
去之前,韩秀在信里告知,她手里还有一些清阁先生写给她的信。我去后,可跟她一起整理,觉得有研究价值的,可带回。我自然充满期待。
细心而严谨的韩秀,将三个大信夹摆在我面前:第一个信夹不用翻检,很整齐,里面全是清阁先生写给她的信,共十七封;第二个信夹里有许多人的信,匆匆看过,发现还有清阁先生写给她的另五封信;第三个信夹里,除一些所转别人信件或稿件的影印本,还有一些台湾《联合报》稿费底单的复印件。
她让我把第一个信夹先拿走,余下的两个信夹,等有时间再一起整理。结果,在华盛顿两个星期,每天行程满满,除了预先安排好的四场演讲,参观博物馆、逛艺术节、看电影、吃海鲜外,我还独自去了一趟位于佛罗里达州最南端,也是美国大陆最南端基韦斯特(Key West)小城的海明威故居,一晃就到了24日,要去纽约。28日下午,在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工作坊”做了题为《老舍:一个自由写家的悲剧》的演讲之后,坐当晚的夜车于次日晨返回华盛顿。
从时间来看,当从波士顿发出的列车启动时,韩秀正在整理那些信件和材料,并将它们装进一个大信封。她在信封上写道:
多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为台北《联合报》副刊所转信件、稿件、稿费的实证。
多半都关系到清阁先生。
在傅光明所做的大量研究中,这些资料或有参考价值,全数交傅光明。
——韩秀
2012年4月28日夜
29日,收拾行李,将一个大信夹,一个大信封,装入随身携带的行李箱。
回京后,我先将大信夹里的十七封信录入电脑,在觉得必要处做了“编注”。收到电子文档的韩秀,除了修改录入时的文字误植,又为每一封信写下不可或缺并颇具意味的“谨识”或“小注”。
之后,我将其他信件输入电脑。5月8日,韩秀除为这些信加了“小注”外,还特意在信前补写了作为收信人的阐释性文字:
2012年4月28日,傅光明下午在哈佛演讲毕,搭夜车自波士顿返回华盛顿,抵达时已经是29日上午。30日上午,他将搭机返回北京。本来准备与他一道检视这些旧信,无奈时间太少。28日夜间,担心着他路上辛苦,甚至焦虑着他也许在睡梦中错过了站。毫无睡意,于是将两个大信夹打开来一一翻检。这两个信夹的内容包括一个长长的故事。其中一个信夹上注明其内容关系到端木蕻良、赵清阁、袁可嘉三位先生。另外一个只注明为大陆作家与《联合报》所转信件、稿件、剪报、稿酬。
1983年夏,我随外子驻节北京美国大使馆。台北《联合报》系名主编痖弦先生便嘱我向大陆老作家约稿。开初极难,写信到作家协会寻找吴祖光先生,信被退回,上书“查无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