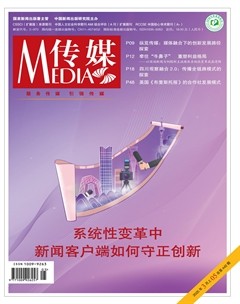摘要:智媒时代为高校思政工作的开展创设了“新界面”和“新基建”。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深度镜鉴约翰·彼得斯的传播观,能够为高校思政工作的智慧化开展拓展新思路。从批判和整合的视角来看,前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单维的传播范式阻碍了思政育人的效能延展;智媒时代“对话”的传播观使高校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和互动,建立起开放、互动的思政教育平台,促进思政教育的双向传播,使学生成为思政教育的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技术与人文融合的大趋势下,应充分发挥智媒时代媒介的“泛在化”与“交互性”特征,促进高校思政工作深度优化。
关键词:智媒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 约翰·彼得斯 对话 传播观念
技术动因常常是系统优化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在智能媒介的嵌入和融合的现实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如何搭乘人工智能这一技术“快车”,不断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向纵深发展,需要思政工作者从多种维度、多元视角、多门学科出发,寻求技术与理念、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缔结点。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和文化理论家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传播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切的理论路径。彼得斯的观点强调了言说的复杂性和沟通的难度,对比了“撒播”“对话”和思想的交流等范式,旨在阐明传播和媒介如何影响交流。彼得斯直言:“交流已经不是一个考虑如何打磨自己的思想工具,使它们能更加精准运输精神内容的问题,而是一个考虑如何去建设一个人们更加公正参与其中的、充满爱心的生存环境的问题。”他关注言说的多样性和言说行为的意义,认为传播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构建社会关系和认知世界的重要手段,并将西方人文主义色彩的经典传播范式细分为“撒播”的传播观和“对话”的传播观。
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的教育模式和传播方式已经难以契合学生多样化的思想需求和信息获取习惯。因此,我们可以从彼得斯的传播观中汲取灵感,从自我言说到思想对话的角度重新审视高校思政工作的技术理论与实践。彼得斯传播观与高校思政工作之间有何联系?前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传播逻辑有何问题?如何在彼得斯的传播观视角下优化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实际效果?笔者将以彼得斯的传播观为理论基础,探讨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工作中的技术理论与实践。
一、自我言说:前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传播观念之困
前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实际流程中体现出信息单维度传输的外部表征。这种方式在覆盖面上促成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广度延展,且与彼得斯对“撒播”范式的推崇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是在纵向深入发展层面仍然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前智媒时代的高校思政工作以传播广度为目标,力求所传播的内容能够覆盖足够多的个体。“撒播”是一种单向的交流方式,这种传播方式在人类的传播中是最悠久的。在前智媒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传播模式中,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由教师作为中心向学生传授思想和知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导致了信息量“大而泛”,学生被灌输大量内容,但缺乏互动和个性化的体验。这也使得学生在接受思政教育时缺乏主动性,限制了其思想开放性与创造性的发展。
在前智媒时代,信息传播主要通过有限的渠道和方式进行。在高校这一特定限度的场域内,教师作为信息的主要传播者,通过课堂讲授等传统方式向学生传递思想和知识,却缺乏学生对信息的反馈和回应。这种缺乏互动的模式导致了思政教育与学生之间的脱节,也使学生对思政教育缺乏兴趣和动力,难以将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除此之外,由于思政教育的结果不易量化,难以评估教育效果,这使得思政工作的效果难以被客观地衡量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