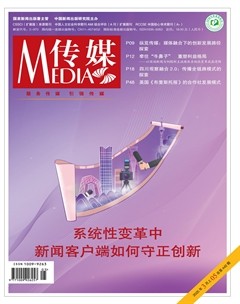在人类历史的延续与发展过程中,文化记忆是文明意识的衍生,其表现为对历史的坚守,对传统的怀旧。文化记忆指向遥远的过去,又紧密地连接着当下与未来,帮助现代社会的个体与群体构建身份认同与归属感,人类文明亦因此在继往开来中走至今日。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形式,文化记忆涉及多元层面,囊括了丰富的意涵。从李清照的词作《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到马尔克斯小说的《百年孤独》,从德拉克洛瓦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到鲍勃·迪伦的民谣《Blowing in the wind》,文化记忆已潜移默化地渗透至众多艺术形式的创作和表现中。
《简牍探中华》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打造的文化节目,该节目聚焦部分简牍出土地,通过“实地探访+实景戏剧+文化访谈”等多种表现形式,讲述简牍古代起源、近世重现、现代研究传承的不朽篇章。2023年至今,随着《简牍探中华》等节目的热播,中国传统类文化节目愈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文化记忆亦成为重要的观察视角之一。节目聚焦数个简牍出土地,通过考古地探访、影视剧情呈现、专家座谈等多种节目形式,讲述秦汉简牍自前朝的诞生与普及、发展与流变,到如今的发掘与保护、解读与研究的传奇故事,再度引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探讨。笔者从简牍及节目的文化记忆是如何建构的、其影像书写的叙事路径是怎样的、最终文化记忆又彰显了怎样的意义旨归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从简牍到《简牍探中华》:文化记忆的双重建构
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简牍承载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语言符号系统、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等,为后人提供研究传统文化的窗口,凸显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文化记忆建构强调记忆并非单纯过去事实的存档,而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被重新构造和赋予新的意义。当简牍成为文化载体时,它本身的存在性和后人的释读是对相关文化记忆的直接建构。作为一档简牍题材的文化节目,《简牍探中华》是对原始文化记忆的重新建构。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再生,通过现代化影像数字将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想象交织在一起,绘制出社会的共同图景,令众多个体在无限的时间轴上找寻到自身的位置。
1.历史的印痕:文化记忆的载体。《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反映了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关键的两个层面。祀,即反映宗教信仰和礼仪制度的祭祀活动。戎,即代表国家安全与君权行使的军事活动。仪式产生于人类文化中的祭祀活动,是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简牍中关于祭祀的记载直接表达君王与百姓对天意的敬畏与顺从,在彰显中华先民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的同时,展现了信仰与礼仪制度在古代社会中的教化与协调功能。如里耶秦简中记载的秦统一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前往泰山祭拜天地,阡陵县百姓于同一时间顺应朝廷办祠先农仪式。仪式的展演和集体成员的共同参与使其成为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诸如此类的传统仪式通过礼仪与宗教来教化民众,强化社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增强社会凝聚力与人民的身份认同感,彰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信仰和文化价值上的共识,描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面貌。
作为战争历史的实录,简牍不仅呈现战事的细节,亦深刻揭示战时社会的复杂动态及其对个体命运之深远影响。简牍内对兵戎相见,对英雄事迹的记载呈现了战争的前因后果、参与者个体的言行举止、悲欢离合与浓墨重彩的家国情怀。这些简牍与传世文献相互映照,为后之览者提供验证、研究、理解历史的依据。中华民族得以构建一个共有的过去,民族记忆逐渐被社群所共享,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跨代传承的文化记忆。
2.古老媒介的光影重现:赋形文化记忆的《简牍探中华》。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期,到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人类历经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其中充斥着兵荒马乱与生离死别。节目弱化关于战争、祭祀等相对血腥暴力和封建愚昧的成分,但又并非完全遮蔽,而是通过重新解读与呈现,探讨这类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同时,节目聚焦于个人与家庭、国家的命运,强调个体的价值、家庭的重要性及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的现实。
文化记忆的构建与传承依赖于叙事。节目以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将个体经历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不计国家被秦灭亡之前嫌,自发为百姓宣讲秦法以避免其因无知而遭受惩罚的官吏禄,还是一生清正廉洁,全心全意造福一方百姓并誓死保卫家园免遭侵害而最终为国捐躯的官吏乘,他们皆是牺牲个人利益而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芸芸众生的典型代表。节目选择性地再现重构与简牍相关的历史场景与文化背景,创造一系列虚拟的“记忆场所”。它们不仅是过去的象征性再现,也是现代观众与历史连接的通道,将个人与家庭的故事置于大时代命运的背景下,展示个体经历与集体历史间的内在关联,强调即便是普通人的生活选择与行动,亦是国家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聚焦个人日常生活与家庭情感世界,有助于将宏大叙事转向更为细腻真实、平易近人的层面,由“大历史”转向“小历史”,其中个人的情感体验、言行举止与国家的宏大叙事水乳交融,构建了更为多元立体的历史文化认知。
节目实景拍摄环节将摄像机对准简牍出土的具体地点及当地博物馆,利用有限的空间作为记忆的锚点,将过去的历史事件与具体的地理位置相连接,以此强调文化记忆与特定空间的关联性。观众置身于其中,看到了简牍实物及其曾经存在的环境,视觉与情感上的直接体验为人们提供强烈的历史真实与沉浸感,加深其对历史事件空间化背景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