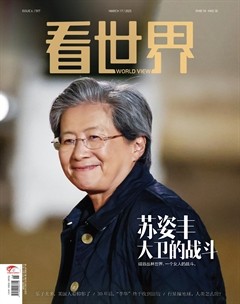建筑师也有他的悲悯。
多年前,我采访成都建筑师刘家琨。主题是一个女孩的纪念馆。他告诉我:“我害怕把别人的痛苦弄成一个题材,自己来做创作。”
设计时,他想尽量做得朴素一些,不用太豪华,那只是一个为普通人而建的纪念馆。他警惕宏大的理念、叙事和意义。选址在成都以西40公里的安仁古镇,那里有庞大恢弘的博物馆聚落,但纪念馆很小,19平米,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博物馆,也可能不是,他本人也不清楚。
外观是帐篷形状,这是几乎本能的选择,也没特意想过灵感。青灰外墙,略显粗粝,内里却通体粉红—十来岁的女孩通常会喜欢的颜色。四面墙,陈列着40余件不能称之为藏品的藏品,文具、衣物、成绩单、评定表、大头贴、老旧字典等普通生活用品。这些寻常物品,勾勒着一个女孩16年的生命轮廓,没有浓墨重彩,只有一些平淡无奇的线条,她的学习、爱好、梦想、她的爱,以及那些戛然而止的瞬间—有裂纹的手机,定格在2008年5月的《萌芽》杂志。
女孩名叫胡慧姗。1993年出生的她,生命只持续到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或许更久一点,她就读的都江堰聚源中学轰然坍塌,废墟之下,她挺了多久,卒于何时,没人知道。她是汶川大地震中87150名遇难者之一,因为这座纪念馆,她没有成为一个冰冷的数字。
当年,地震发生后,建筑师刘家琨前去赈灾,在残梁断柱间看到了一位心碎的母亲。她捧着遇难女儿的脐带和乳牙,试图感应其灵魂。这深深抓住了他。刘家琨提出想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但对方说,经济困难可以克服,心灵的创伤没办法抹平。一个月后,他忐忑不安地找到这位母亲,试探性地提出为胡慧姗建一座纪念馆。他心情惶恐又复杂,怕自己站的角度过于微妙。但对方听了感激涕零,当场跪下。
刘家琨的建筑生涯里,可以称之为代表作的有很多,如西村大院、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水井街酒坊遗址博物馆等,但胡慧姗纪念馆是其中最小、最特殊的建筑。有人问他:你知道这是个象征吗?他没有反驳:“我知道,现在它成了一个象征。”
今年3月4日,69岁的刘家琨,摘得2025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国际公认的建筑界最高殊荣,有“建筑界诺奖”这一说法;上一次拿奖的中国建筑师,还是13年前的王澍。评委会说,刘家琨将乌托邦与日常生活、历史与现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等看似对立的事物,编织于一炉,他秉承建筑环境的超越性力量,激发人文关怀,升华人类精神。
我想换成一个词,就叫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