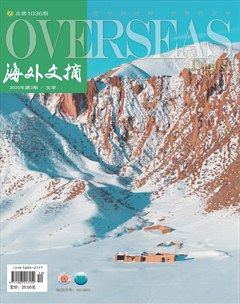我像农民爱惜土地一样珍惜每一页稿纸。
自从东汉时期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中国人一般就不再把汉字写在龟壳、石头、羊皮、竹简、丝帛等物件上,开始写在纸上。纸张的运用,无疑等于引发了一场书写革命,使具有书写能力的文人们仿佛一下子走进了广阔天地,写作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作品产量迅速增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纸张作为载体,也许不会有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和长篇小说四大名著等。绘画和书法对纸张的依赖性更强,好比庄稼的生长离不开土地,绘画和书法也离不开纸张。纸张的出现,才催生了我国真正意义上优秀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不管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还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无不得力于纸张的功劳。久而久之,纸不再单纯是一种物质,它与文化紧密相连,几乎被文化同化,变成了文化纸。我们每个人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也必然是从接触文化纸开始的。
在上小学之前,我每天能摸到的最多的东西,无非是泥巴、野草、蚂蚱、螃蟹、小鸟儿和一些能吃的红薯、胡萝卜、浆果儿之类,很少摸到过纸。入学后,我开始捧起课本学念书,对着作业本学写字,糊里糊涂地觉得,字就是纸,纸就是字,字和纸是一体的。我没有把字和纸分开,没有把纸单独择出来,更没有意识到纸的重要。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才使我对纸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是用毛笔蘸着墨盒里的墨汁写字。学校不发作业本,我家也没钱给我买作业本。可不写作业又不行,急需作业本时,母亲就卖一捆干草,或两个鸡蛋,换几分钱给我。我到集上买回一张白纸,裁开,用棉线钉成本子写作业。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眼看作业本快用完了,就跟母亲要钱买纸。母亲卖了两个鸡蛋,换五分钱给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枚大个儿的、十分完美的钢镚子。钢镚子还很新,通体闪耀着银色的光泽。我把钢镚子放进一只空火柴盒的抽匣里,带到学校里去了。我拿起火柴盒在耳边摇晃,听见钢镚子在里面哐啷哐啷响,很是好听。不仅如此,我还跟同学借来蜡笔,把钢镚子垫在课本的空白处下面,在上面涂。来回轻轻一涂,钢镚子上的美丽图案就显现出来了。不一会儿,我课本的空白处就出现了不少彩色的“钱”。说来我是过于显摆,以致露了“富”,被哪个不开眼的同学瞅见,趁我课间在校园里玩耍时,就把我的钱连同火柴盒一块儿顺走了。等我回到教室,发现钱没有了,顿时傻了眼。当天是星期六,我打算的是星期天去集上买纸。如果买不到纸,下个星期一就无处写字。字不能写在手心里,不能写在课桌上,更不能拿空气当纸使,我怎么办呢?我是那么喜欢上学,而当学生的不能写作业,这学还怎么上呢!事情被我想象得越来越严重,于是我就咧嘴哭了起来。我是班里的班长,同学们听见他们的班长哭了,都很同情,纷纷围过来在我面前洗刷自己。还有的同学悄悄向我提供线索,说我的钱八成是被一个姓范的男同学偷走的,还有人说可能是那个姓张的女同学偷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