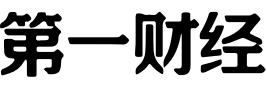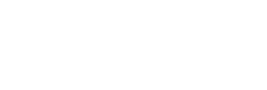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
意大利拉文纳/博洛尼亚
走海路的好处,醒来已落在一个不易抵达的陌生港口。今晨泊靠意大利拉文纳港(Ravenna),近亚得里亚海,码头堆满各色集装箱,多是地中海、马士基、中远海运、长荣等国际货运大公司的,此行最熟悉的景象之一。港口货轮连接全球物流贸易,它们是全球化的仆人,也是地域冲突的囚徒。彭博(Bloomberg)数据终端上有个服务,可实时跟踪全球任何一条货轮的信息,实时位置、吨位、货物及航程详情。临近大港口,屏幕上就爬满了小蝌蚪,那是等候进港装卸的货船。拉文纳出身显赫,它曾是西罗马帝国晚期和东哥特王国首都,也是东罗马帝国的意大利首府,以古罗马帝国建筑遗迹出名,人称意大利“拜占庭”。小城区区10万人口,却占了8个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是意大利的家底。
我们决定不去150公里外的威尼斯,自驾去更近的博洛尼亚(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首府),只因为从没去过。博洛尼亚城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有最地道的中世纪遗迹。我住在伦敦近20年,去意大利稍多,特别是威尼斯,一个唯美但奄奄一息的水城。英文有个词decadent,通常被直译为“颓废”,似乎未得其寓意。其实颓废也得有品,有格调,于人于物于自然皆如此,而decadent暗指美极而朽,需要丽质与极致情趣。威尼斯与海相连,如贵妇人美而衰,称其decadent再贴切不过。某年去威尼斯,潮水漫过腥咸的运河,贡多拉舵手哼着歌剧穿行,众人在圣马可广场赤脚蹚水,听维瓦尔蒂的《四季》,掩不住的却是末日之感。漂浮的威尼斯,仍支撑着不可逆的沉降,原住民现不及千人,全城更像电影布景,每天上场的是全球的群众演员。旅行时,我们奔古迹与美物而去,潜意识里还是膜拜时间,膜拜适者生存。无论雅典神殿、开罗金字塔、墨西哥奇琴伊察,还是西安兵马俑,墓葬或祭祀神庙,只要留下了,就成了文明。
旅行,更是存在主义的游戏,与你心境有关。旅途中的愉悦或郁闷,源自每天碎片的体验,一次问路的冷遇,一家餐厅的猫腻,一个厕所的高价“门票”,都可能使你潜意识里抹掉那个地方,从不回返。旅行中的人,水土不服,最是外强中干,紧张、脆弱且多疑。每次进出码头机场车站酒店,都被问你是谁。护照,不过是身份的纸牌屋。


我们喜欢走小道,麦田已呈浅黄,路边有鸡跳出,电线上站麻雀,像一个个墨点。不远处有狗横卧,我们放慢车速,它不情愿地让了道。地平线上,一长条暗黄的色块,应该就是博洛尼亚城了。我们往老城开,建筑外墙由黄换成赤陶的红或者暗橙,中世纪在靠近,灰石板路越来越窄,有误入死胡同的恐惧。城中心兜了一圈,每个车位都有主,该死的蓝线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奢侈的东西。人是本能的功利动物。小广场上,我拦住正将咖啡机装车的中年男子。他不说英语,索性趴在车窗帮我查手机地图,指指八八广场说那儿有付费停车场。10天前,3.6亿欧洲人参与了欧洲议会选举,不出所料欧洲的政治天平继续向右倾斜,民粹政党在法、德、意等国支持率都明显上升。正在位的梅洛尼就是得益者。这位意大利历史上首位女总理曾表示崇拜墨索里尼,贝卢斯科尼是她的政治教父。意大利人对政治冷感,这次投票率不足50%,街头已不见任何竞选海报或选战的痕迹。
我喜欢意大利,因为它的阳光与亚热带地中海的温润,它的随性与烟火气,从美食、大家庭气息到悦耳的意大利语,连残忍的黑手党似乎都讲义气人情。旅行是短期行为,对一国一城一地的好感或恶感,容易被放大或走极端,最易收获一堆自以为是的偏见,无论赞美还是吐槽。前方尽头是博洛尼亚的地标,即出名的中央双子塔楼“DueTorri”(Asinelli和Garisenda),并排挨着。据说9·11事件中塌毁的纽约双子塔,设计灵感就源于此。此双塔建于12世纪初。它的名气与比萨斜塔同病同源,因为都长歪了—比萨斜塔的头歪得更多,名声自然更大,塔顶比垂直线歪了4.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