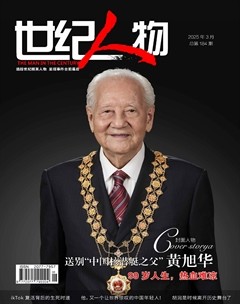最后看一眼700平的大院子,告别自己在新西兰的“家”,刘璐拎上行李,和丈夫、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出国10年,她已从青涩的留学生蜕变成有房有车、工作稳定的“新纽村人”,过上了别人羡慕的舒适生活。可即便如此,她还是选择了离开。
移居加拿大近20年的水哥一家,比刘璐更早踏上回国的旅程。为此,他前前后后砸进去二十余万:航班不断改签,一家四口干脆买8张机票,哪趟能飞坐哪趟;仓促给孩子安排的学校不理想,又为择校交了14万“学费”……
但水哥认为一切都值得,“回到香港这段时间,感觉颇似一次重生。”
像刘璐、水哥一样回流的人还有不少:在德国的陈乐,发现自己身边一半的同胞都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英国事业蒸蒸日上的玛丽也选择回来过日子。
越来越多向往不同的生活,甚至怀揣着移民梦远渡重洋、奔赴异国他乡的人,如今正排着队,踏上回国的路。
社媒平台上,热门移民国家相关话题,充斥着滤镜破碎的声音,“移民回国”“反润”的话题热度也持续攀升,分享量破万。
当梦想照进现实,总是在寻觅更好更舒适生存环境的人们,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故土。
一、中国人只是爱有滤镜的“自由生活”?
宁静古朴的街道、海港夜景装饰的落地窗、沾着热汗的球拍……陈乐挑选的“快乐碎片”,可以凑一部欧洲生活松弛感图鉴。
她按下发送键,熟悉的红色数字即刻跳动,国内亲朋好友们纷纷前来点赞,评论区很快被“你的日常是我的诗和远方”“替我自由”等艳羡的声音填满。
然而,陈乐却有苦说不出——这些看似惬意、悠闲的娱乐活动,只不过是她抵抗抑郁的努力而已。
到德国近10年,她还是不能习惯漫长冬季里,连续几个星期看不到太阳的阴雨绵绵。下午三四点暮色西垂,走在低矮的云层之下,一股被流放“宁古塔”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为了对抗“winter blue”(冬季抑郁),她不得不把30天的年假安排得满满当当,只为寻一处阳光海滩调理心情;家里更是常备“人造太阳”、毛绒玩具等摆设,营造温馨氛围感。
“在国内,运动、旅行很多时候是锦上添花,但在德国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她无奈道。相比之下,在新西兰生活的王宥恺,生活环境就好上许多。
初到风景如画的新西兰,他就被那里漫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草场所吸引,随处可见的公园、湖畔,更是让他不禁感叹:“每一帧都美得可以截下来当壁纸。”
但再漂亮的景色终有看惯的一天,最初的震撼过后,地广人稀的孤独感开始翻涌上来,尤其作为天生爱社交的北京人,找不到人唠嗑这件事,抓挠着他的心肝。
“大家都住得远,不可能像国内一样经常去聚会、串门。”王宥恺说,而且在国外,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很强,聚一次得提前几天预约,缺了一些“说走就走”的爽快。
加拿大老移民水哥也发现,打破滤镜的西式生活,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的体质。
犹记得打完新冠疫苗后,在家跳绳锻炼身体的他,突然心脏剧痛,双腿发软,瘫倒在地。
他强撑着爬起来,给家庭医生打去电话,对方左一句“我对您现在的状态非常关心”,右一句“我已经清楚您的需求”,情绪价值拉满,最后处理办法却是:情况紧急,我们帮您联系专科医生处理。
辗转到专科医生那里,上述的车轱辘话又循环了一遍,再问看诊时间,水哥人都傻了——排期约到了3个月之后。
“如果当时我患上的是心脏病,后果真的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