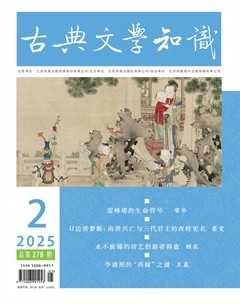酒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恐怕没有人会怀疑。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把酒与诗的关系说得很直接,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喝酒的李白,到底会写下怎样的诗篇,或者说不喝酒的李白还会不会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
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酒是舒缓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说只有酒能解忧,就太绝对了,不喝酒的人有了忧愁怎么办呢?所以酒并不是解忧的唯一方式,何况酒也是助兴的一种物质载体。有忧愁可以喝酒,有快乐也可以喝酒,甚至无聊寂寞,也可以斟上一杯酒,或许在这个时候,就真的是酒中岁月长了。
酒在古代也是应对不良政治的佳品,魏晋时期司马氏政权,排斥异己,杀戮成性,阮籍担心说话暴露自己的政治态度,就以醉酒度日,一醉就是六十天,以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保全了自己。刘伶用酒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醉酒后放浪形骸,行为常常匪夷所思。更荒唐的是他年轻时坐鹿车出行,随身带着一壶酒,让人拿一把锄头跟着,说“死便埋我”,也就是我在哪里喝酒喝死了,就把我埋在哪里。酒实际上成为刘伶这一类人的一种生活。
以上无论从调节情绪、文学创作、应对政治和参与生活等各个角度来看,酒与一个人的精神修养、行为意识和文化心态密切相关,简单来说,酒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生命的载体。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与酒的关系相当特殊,他特别好酒,但酒量又比较差,或可以用“小高快”三字来概括:酒量小、兴致高、醉得快。他自己说有三不如人:唱曲、饮酒与下棋,饮酒果然是他的弱项,但他能得酒趣,就像他说唱曲不如人,却是填词高手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兴趣与感受不一定成正比。我们看他怎么说自己喝酒: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书东皋子传后》)
这简直是一段神奇的文字。苏轼说,关于喝酒,我有两个天下第一:一是天下最不能喝酒的人;二是天下最喜欢喝酒的人。要把这两个天下第一放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真的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苏轼居然做到了,可见非常之人果然有非常之事。看来苏轼的“好饮”只是说创造饮酒的氛围,他自己说,大家在一起,即便自己不喝,就是看着客人端着酒杯,心里比客人还要舒畅,好像酒进了客人的肚子,而酒意到了自己这里。苏轼因为多次被贬,闲居的时间也就特别久,而一旦闲居,到访的客人也就特别多,客人来了当然要摆酒,苏轼说的好饮就是喜欢招待客人饮酒的意思。他一度说恨不得“移家酒中住”(《和陶神释》),那是因为喝酒既然是一种生活,直接生活在酒中,就省掉了造酒、买酒等程序,进入一种要喝酒便来,喝醉酒自去的境界。
关于酒量问题,苏轼一直比较低调。他一再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题子明诗后》),“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叙),“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把自己喝酒的身段放得很低,只是说自己爱喝一点酒,这到底是故意做个姿态之语,还是实事求是之语,就需要我们仔细去分析了。
苏轼说即便喝上一整天的酒,也就是“五合”的酒量。这个“五合”在今天到底是多少的量?可能要作一番推算才能大致了解。五合相当于现在的半升,也就是332毫升,50毫升相当于现在的一两,那苏轼喝一天酒,总量差不多有六两多。能喝六两多,看起来也不错了,但你要知道苏轼喝的是黄酒或者果酒,酒精度一般在15度上下。关键这六两多的酒还是喝一整天的量,这个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苏轼的酒量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譬如在惠州,他就说过“弟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尔”(《与程正辅》四),状态佳胜,似乎也有大饮十三银盏之例,但无论如何,苏轼的酒量总是偏少的。酒量差的人一般尽量回避喝酒的场合,而苏轼居然每天要整一点。所以我们知道,在苏轼看来,喝的不是酒,喝的其实是一种心情。苏轼说“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倒是一句很老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