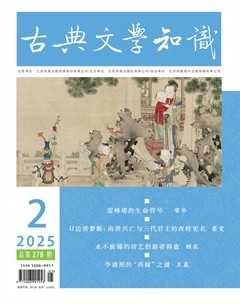骗婚谜团
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赵构自绍兴府移跸临安。按照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记载,她在此年也抵达了杭州城。这一年,李清照四十九岁。
从李清照自己的叙述来看,在暮春三月,或至迟在夏季四五月间,她大病了一场。如果这确乎属实,那么尚在病重之时,胞弟李迒竟陪着一个人来向李清照提亲。
这是李清照生涯中一桩重大的事件和谜团,即易安居士的“再嫁”问题。
且先看她后来所写的《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中是如何描述这一段上门提亲过程的,节选如下:
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应门惟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舌,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黾俯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
按照信中文辞,李清照当时可谓病入膏肓,已神志不清,甚至连丧葬所需都置办了一些。如“牛蚁不分”即用《世说新语》之典,谓病重后“闻床下蚁动,谓之牛斗”;“灰钉已具”指棺椁所用的石灰、铁钉等已准备妥当—但这些陈述很可能有所夸大,岂有将死之人,再改嫁他人者?
清照随即引出胞弟李迒。她以骈文的形式暗示,寄居“弱弟”宅中,虽有其侍以药石,但寻常也只有一个老仆而已。所谓“老兵”,可能是过去亡夫赵明诚为封疆大吏时随身的傔人仆从,如《金石录后序》里所说的“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的“故吏”。细读之下,“弱弟”很可能还不是只针对提亲、再嫁一事,或许还指向“惧内”。因为在李清照的叙述里,弟媳之类的亲戚是缺席了的,以当时之伦理和男女大防观念来说,一些必要的起居照顾和服药治疗等事,当由女性亲属来更为方便。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胞弟李迒的妻子对李清照寄居家中已颇为不满,因此李清照才在年近五十的时候,甚至可能在重病中,被弟弟再嫁了出去?
这时候那位提亲者仍然半藏在叙述造就的帷幔中,只说他巧舌如簧、口蜜腹剑。真正关键的信息所提供的细节在这一句,“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什么是“官文书”呢?简单来说即“官告”(告身),它是一种宋代官员身份的重要凭证,北宋神宗朝元丰改制后就由官告院改吏部来颁发官告。而宋代之“官员”,乃是官、职、差遣相分离。官者一般指寄禄官(本官、阶官),代表品级;差遣指职事官,代表实际工作,这个才相当于今人所理解的官职;职者则代表文臣的殿阁职名、武将的阁职等“加官”。元丰改制后,一般以“凡入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的原则授予官告,不论是授予阶官、差遣、还是封赠、加勋,只要入品级,就会给官告。
以赵明诚生前为例,当时他移知湖州前,结衔为:朝散大夫、秘阁修撰、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路经制副使。其中,朝散大夫是从六品的本官;秘阁修撰是从六品的贴职;而知江宁府以及江东经制副使则是差遣,其中江宁府知州当为正六品。
宋代的官告必须写明三代、乡贯、年甲,且抄录制词全文,并有主授长官和承办吏人的签名或用印,这是极其难以伪造的。不妨以南宋孝宗乾道二年《司马伋告身》为例,看一下南宋的差遣官告身是怎样的:
从而可见,要做一份假的官告何其困难,需要伪造不知多少朱紫大员和主事官吏的签名、押字(其中地位高者只需要签“名”,而地位较低者需要姓、名连署,这是为了责任追查),谁能做成这样的事情,然后再骗过一位本身就在当时朝廷中枢的官员?
李清照的胞弟李迒并非寻常百姓懵然无知,而是身在行朝,作为宰执属官(敕局提举一般为宰执大臣),他对百官除授的流程、三省堂除或吏部铨曹、官告院的官吏也应当很是熟悉,想要骗过李迒,几无可能。
真假“张汝舟”
如今一般认为,李清照改嫁的这个后夫是一位低级官吏,名叫张汝舟。巧的是,当时另有一个张汝舟。须经对比才能见出其中问题。
一为毗陵(今江苏常州)张汝舟,系北宋徽宗朝崇宁五年(1106)进士,宣和二年(1120)已任殿中侍御史,此为台谏要员,此后在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由朝奉郎、明州知州调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直到次年六月再补外知明州,并带直显谟阁贴职。
一为阳翟(今河南禹州)张汝舟,可查得于绍兴元年,以右承奉郎差往池州措置军期事务。
毗陵张汝舟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且曾任殿院御史。他担任的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一职虽然已远不能和北宋熙宁变法时候的“都检正”(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相提并论,但仍然是一个朝中极其重要的中层官职,一般负责通进司与中书门下省之间一系列公文的上传下达等工作,官正六品。其本官朝奉郎也属于正七品朝官。宋代文臣的本官分“京官”与“选人”,其中绝大多数文臣都终身处于“选人”的官阶,他们大多只能担任州县长官的幕职僚佐或其他底层职务,一切重要的差遣通常都与他们无缘,因此由“选人”跳“京官”是第一道极难的关卡,当时视为跃龙门,否则就是“老死于选海”。而“京官”又分“朝官”和普通“京官”,只有到“朝官”级别才能有望担任重要差遣,成为中层甚至高层官员。
阳翟张汝舟则大不同。首先他的本官是右承奉郎,这是正九品的京官,属于文臣京朝官三十级官阶中的二十九级,差毗陵张汝舟的朝官朝奉郎阶有六阶的巨大差距。并且,其“右承奉郎”之“右”代表他并非正经的进士出身,而非正式出身的官员,在宋代要成为朝官是比较困难的,前途一般较为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