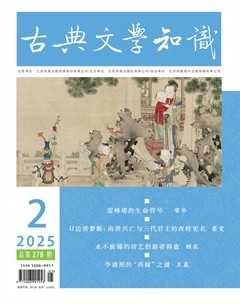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墨守成规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要付诸实践,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诗歌这种文学样式里,有着无比丰厚的传统,跟着历代相传的体例走,不仅比较容易入门,甚至也不难成为行家里手,获得大家的认可以至于好评;而创新则很难,弄不好就容易失败,沦为所谓“失体成怪”。任何领域里异类的日子大抵都不大好过,诗坛上的异端就更是如此。保守派和庸众的吐沫能够把胆大的才子淹死。
一方面讲究继承传统,一方面又花大力气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来,诗歌史上曾经不断出现这样的勇士,而中唐的大诗人韩愈(字退之,768—824)更是其中投入力度很强、终身从事诗歌创新的豪杰。有不少人,在资历尚浅时不敢创新,诸事小心谨慎,但求立足站稳,到中年更加油腻,他们也许能够实行所谓衰年变法,而更大的可能则是就在老路上走到底;另一些人青年时代锐气十足,显露锋芒,出人头地,而一旦站稳,特别是功成名就之后,就爱惜羽毛,只想保住已经到手的利益和名声,未老先衰了。韩愈则不然,他从事诗艺的探索革新起步甚早,而又终身不懈,开创了新的流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贯穿到赵宋以及更晚的时代。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韩愈这首《山石》诗以某次出游途中投宿古寺的经历为中心,写自己的见闻和感慨。这座寺庙隐藏在风景秀丽的山里,走了很长一段崎岖狭窄的小路,抵达时已是黄昏了。僧人热情地请自己参观这里古老的佛像壁画,可惜光线黯淡,实在看不清楚;主人又热情地为我安排食宿,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心情激动,反倒睡不好了。第二天一早下山,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随着山形出入高下,一路的景色美不胜收,古木参天,山水的色彩丰富极了,其间又曾赤脚过山涧,令人十分兴奋愉悦。这种温馨自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什么要在官场里打拼,接受种种人事的牵制约束呢?我们这些人要赶紧觉悟、早日回归自然,千万不能死守官场往而不返啊!
这次难忘的旅行让韩愈深深地感受到,失去官职枷锁以后的一身轻松。
记叙外出游览投宿于寺庙的诗篇在唐代并不少见,但一般不大会像韩愈这样来处理。例如杜甫早年有一首《游龙门奉先寺》,诗云:“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这里舍去各种细节,只是虚写其景;而韩愈此诗则“当境实写”(陆时雍《诗镜》卷三九),所以他要采取七古的形式,以便作出必要的展开。
钱仲联先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将这首诗系于贞元十七年(801);又引用清人方东树的意见说:“不事雕琢,自见精彩……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昭昧詹言》卷十二)前人又曾一再说起韩愈的“以文为诗”。这首诗的艺术手法确实很像一篇散文,诗中明确提到“黄昏”—“夜深”—“天明”,全篇按照这样的时序来叙写此行的所见所感,这与常见的游记散文几乎如出一辙。诗中有些句子也很像是散文,如“黄昏到寺蝙蝠飞”“时见松枥皆十围”等等。韩愈原是散文高手,在诗里嫁接一些散文句子,正是轻车熟路。
诗中描写的这座寺庙似乎在洛阳远郊。韩愈从贞元十五年(799)秋天起在徐泗濠节度使(驻节徐州)张建封(735—800)的幕府里充当推官,这里规矩很严,上班要晨入夜归,时间极长而毫无必要,对此韩愈曾尖锐地提出书面意见(《上张仆射书》)。张大人喜欢打马毬,往往失去节制,韩愈又一再提出劝谏(《谏张仆射击毬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韩愈这样一再顶撞上级,领导虽然也曾表示过嘉许,而心下未必高兴,韩愈的日子也一定好过不了。到第二年张建封去世,原先的幕府解散,韩愈就去了洛阳,寻求新的出路,后来终于得到一个“四门博士”的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