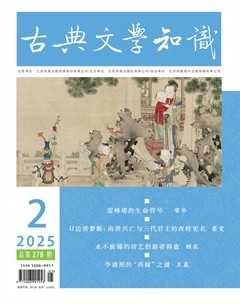古代帝王登基常伴随着一项重要的仪式:改名。这虽不必须,却十分常见,和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密切相关。帝王既是九五之尊,就该称孤道寡,百姓也需要避讳以示尊重。所以,帝王为体恤百姓,往往首选生僻字改名。最常见就是取一个带有“日”字旁的生僻字,例如五代后梁的建立者朱温,称帝后就改名“朱晃”,名中有一个“日”;而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因为其兄长赵匡胤登基称帝,他需要避讳,就改名为赵光义,赵匡胤死后他继位当了皇帝,就又改名为“赵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似乎再没有比太阳更能象喻人间帝王至高无上权位的了。
南唐政权共传一帝二主,将近四十年光景,除了先主李昪在改国号的同时改名,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都是在登基的同时改名。无论是有意识的模仿,还是潜意识的共识,三代君主均以含有日字偏旁的新名字,寄寓自己江山永固,甚至统一天下的美好愿望。而改名的历程也恰巧应合其个体命运变化和国家兴亡的历史。
李昪
南唐开国君主改国号为唐时,改姓更名为李昪,自称为大唐后裔。实际上,各种史料虽然对李昪的出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他伪造自己祖先的线索却都透露出一致的端倪。
以《新五代史》为例,认为李昪本姓李,小字彭奴,字正伦,父亲名叫李荣。他“少孤”,六岁丧父,自幼失怙,原名早已不详,史书上只记载了他的小名:彭奴。中国人起名字一贯有起个贱名好养活的传统,男孩子小时候不好养,就会起一个贱名作小名,而魏晋以来,“奴”字更是广泛应用到长辈对小辈的称呼之中,含有某种特殊的亲近之意。而彭奴不仅名贱,《新五代史》更言他“世本微贱”,身份地位也很低下。但综合各种史料,《南唐史》的作者任爽先生认为:“‘世本微贱’与‘唐氏苗裔’相比,虽较为可信,却同样缺乏根据,结论未免有些草率。”所以,李昪的身世早已不可确考,我们唯一能够确定是他并非大唐苗裔,至于他的父亲是不是李荣,是哪个李荣,甚至他原本姓不姓李,各种资料均存在很大争议。任爽先生据李景达与李德诚之女成婚事认为:“李昪即位的时候,不仅没有冒充唐室后裔的打算,甚至从未考虑自己原来姓李这件事。既然李昪不可能是唐室后裔,而且原来也不姓李,那么,无论哪一个李荣,都不可能是李昪的生父。”(《南唐史》)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身逢乱世,李昪恐怕很难有所作为。但时势造英雄,小彭奴仪表不凡,年少的他流落异乡,遇到后来创立吴政权的杨行密,被惊为天人,《新五代史》的记载是“奇其状貌”。杨行密在这个少年身上看到不可限量的未来,不知他可曾想过这未来是通过篡夺他杨家的吴政权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站在杨行密的角度,会发现他似乎以伯乐自居,把狼当作千里马引进了自己的居室。当然,收养义子是晚唐五代割据政权扩充自己势力、拉拢人才的常见方式。俗语云“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在生死存亡的战场,往往只有至亲骨肉、父子兄弟才能悍不畏死,临危救难,相互配合。而亲生儿子有限,自然流行收养义子。但是杨行密的儿子容不下李昪,因此,杨行密把他推荐给身边的大将军徐温,改名徐知诰,从此这个生而不凡的少年开始拥有了资源和机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屡立奇功;在朝堂上从容斡旋,拉拢平衡,智计不凡,管理有方。
公元937年的冬十月,徐知诰接受吴国国君杨溥的“禅位”称帝,建立大齐政权。时隔两年,徐温的一众子侄请求尊贵的皇帝恢复本姓,徐知诰谦让说不忍忘记徐温的养育大恩,犹豫不决,遂与百官商议,百官联名奏请皇帝恢复本姓。公元939年,已经称帝两年的徐知诰终于“恢复”自己的姓氏,正式改名李昪,同时改国号为唐,自称为李唐王朝后人,声称自己的政权是唐王朝的延续,历史上便把这个政权叫作“南唐”。
其实,南唐和已经灭亡的唐朝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而李昪既然很可能都不姓李,也就更不可能和唐王朝存在血亲关系。逻辑上李昪既然经过充足准备,在登基两年后改姓、改国号,并编造了详细的世系图谱,对其攀附的血亲就该有一致的记录,但各种记载却存在出入:有的说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的后裔,有的说是唐玄宗之子永王李璘的后人,陆游的《南唐书》认为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玄孙,也就是四世孙等,可见这在当时已被传为笑谈,到今天更已不可确考。在政权的初创期,和李唐王朝攀上亲戚,符合这个刚刚建立的王朝的利益。复兴李唐皇室的大旗能够成为一块遮羞布,盖过这场以禅让为名的掠夺,让李昪政权的取得和建立变得更为合理,稳定人心,堵住悠悠的议论之口。当然,在那个不断发生以臣弑君的人伦悲剧的乱世,政权的平稳更迭对于本国的百姓来说已经是福非祸。
“昪”字比较生僻,是日光明盛的样子,犹如南唐的建立,李昪稳固政权后,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举措,使南唐逐渐成为十国政权中疆土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李昪的人生正好大致划分为三段,他的三个名字也正好代表了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彭奴—徐知诰—李昪,字正伦。每一次改名都是一次跨越阶级身份的巨大跃升。
彭奴代表了他悲惨又低贱的童年,即使少年丧父,流落异乡,也仍被杨行密和徐温看重收养;自从成为徐知诰,这个少年开始拥有了晋升机会,开启了他文武双全的名将权臣生涯,甚至取杨吴政权而代之,一跃成为皇帝,建立了徐齐政权;李昪无疑是他人生的巅峰,他建立大齐两年后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自称为唐室后裔,开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辉煌历史。可以说南唐二主尊贵的身份起源于李昪的努力,南唐的日头也果真是在李昪这里升起的。
李璟
和“昪”相比,“璟”的本意是玉的光彩,比“昪”要逊色很多,有什么能比得上太阳的光彩呢?在李昪以至多寻常甚至微贱的身世得到徐温的收养,又与李唐王朝攀上亲缘关系的传奇甚至诡秘的身世面前,李璟改姓更名的过程虽然稍显复杂,却平实许多。
李璟初名徐景通,是李昪的元子,字伯玉,登基后改名李璟。但是李昪、李璟死后,葬在南京的祖堂山(牛首山附近),而南唐二陵出土的重要资料中有玉哀册和石哀册,在李昪随葬的玉哀册中,李璟自称为“瑶”:“维保大元年,岁次癸卯,十子嗣皇帝臣瑶……”(《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我们据此得知,原来在徐景通到李璟之间,他还曾改名为“瑶”,“瑶”就是美玉的意思,和他的字伯玉关联密切,《南唐二陵发掘报告》的撰写者认为李璟在刚登基时曾改名李瑶,后来出于瑶字比较常见、不易避讳的原因,又更名为李璟。这在表面上看来顺理成章,但鉴于“瑶”这个名字在安葬李昪时已经有了,李璟继位前后情况又比较复杂,在一切尘埃落定前应无暇改名,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李璟是被“待如太子礼”时已经为了避讳,改名李瑶,正式登基后又更名为李璟。
中国人名字的中间一个字是记载排行的,所以兄弟之间往往都有一个字相同,到今天也是如此。李璟这一代的排行字就是“景”,所以他的二弟李景迁、三弟李景遂、四弟李景达、五弟李景逿,都有一个“景”字。成为太子、继而成为皇帝的他如果不改名,兄弟就都得改,比如雍正帝叫胤禛,他没有改,他的兄弟就将这个记录排行的“胤”改为“允”。古代制度一旦被立为太子,已经有避讳的现实需要了。例如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初名成德,就是为避当时的太子胤礽(胤礽的乳名是保成)讳,改纳兰成德为纳兰性德。李昪要立李璟为太子,李璟辞让不受,李昪下令臣民通信时用太子的礼节对待李璟,并大赦天下,所以,很可能李璟就是在这时改名为李瑶,登上帝位后,考虑到“瑶”字常见,避讳不便,且不够吉祥,更想取个和日相关的名字等因素,又更名为李璟,同样和他的字密切相关。李璟在治国用人上虽然都是庸才,但也确实是公认的史书里走出来的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
可惜的是,南唐最终在和后周的战争中节节败退,为此,李璟不仅割让了长江以北的大量土地,削去帝号,向后周称臣,甚至仓皇迁都,还将这个耻辱带到了自己的名字上,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以北方政权为正统,南方政权均视为“僭越”,因此记载李璟的名字也都写为“李景”,这是向后周称臣后,为了避郭威的高祖郭璟讳,改名为“李景”,但这个“景”字本是李璟这一代人的排行字。虽然在南唐内部,李璟使用的还是带王字旁的“璟”,但是在官方,他确实已认可了不带“王”字边的景字!堂堂帝王,俯首称臣,还认可了以自己排行字单字为名。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南唐实亡于李璟”,并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这似乎在改名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我们同样来梳理一下:徐景通—李景通—李瑶—李璟—李景,字伯玉。三代君主中,李璟的名字最多,也最复杂:出生时作为徐知诰的嫡长子,徐温是他的祖父,他叫徐景通,是名臣之后;随着李昪称帝建立南唐,复姓为李,他也跟着改姓为李景通,是明主元子;后来被待如太子礼后,改名李瑶,开启了他的准太子生涯,积累了诸多政治资源;登基后又改名李璟,正式成为皇帝;后因战败向后周称臣,削帝号,为避讳改名李景,成为国主,南唐从此再无和中原一战之力,他的排行字成为单名。算来李璟真是频繁地为避讳而改名:在南唐,作为位尊者,他体恤兄弟和百姓;在更广袤的大地上,作为位卑者,他畏惧刀兵和权力,打不过只好俯首称臣,最后的这个“景”字可以说是他的耻辱。
李璟的名字也和李昪一样,可以代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这也并非巧合,一个人会改名,总有些外在或内在的原因,对他个人而言,也往往意味着新阶段的开始。而这就方便我们从姓名入手,掌握南唐三代君主的人生轨迹。
李煜
南唐后主李煜初名“从嘉”,他生于七夕,且生有异表,在李煜的父辈和祖辈看来,他的面相是“嘉”的,是美好的,所以他们希望能跟从、顺应,乃至于印证这份美好,所以取名“从嘉”,字重光,更是比喻累世盛德,辉光相承。正如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屈原列举自己的“内美”,这和我们今天所谓的内在美的概念很不一样,“内美”是与生俱来的美,具体到屈原,就是我的祖先是谁,我的生辰八字多么不凡,我的名字多么美好。即令屈原骄傲的“内美”是自己显赫的家世、不凡的生辰八字和美好的名字。而这些无疑李煜也有,还加上一条:他有不凡的相貌。
他的相貌让父辈、祖辈欣喜的同时,也让一心执着于皇位的哥哥李弘冀颇为忌惮,李煜本人没有野心,于是他就一味示弱,但是居然就靠着退让躲闪获得了国主之位。后世人对李煜的态度往往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是因为没有充分的“理解之同情”的缘故。在李煜看来,如果乱世为王,武略更胜文韬,为何命运要选我上位?要打仗,兄长李弘冀胜我何止百倍?要综合素质,叔父李景遂心机深沉,亦远胜于我。而我能够继位,仅仅由于“内美”。基于先天和后天的养成,每个人都有自我设定和与之相符合的生存策略,并且往往会持续一生,没遇到重大变故不会改变。这个策略因人而异:有人坚信努力才能有回报,有人则秉持宿命观点,这也让他们的人生选择截然不同。对于李煜来说,退让躲闪,与世无争,逃到自己钟爱和熟悉的生活中去就是他的生存策略。换言之,或许就是迷信所谓的“天命”。既然一个人可以靠所谓的“内美”不努力获得王位,难道还不可以靠相同的策略守住王位,甚至光耀南唐的江山吗?过往的经历让他心怀侥幸,李煜登基时,将自己所有期许都放进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名字里,他直接改名为“煜”,是光耀、照耀的意思。他盼望他的天生异相能够给南唐带来好运。换言之,他的自我定位就是“南唐吉祥物”,想荒唐地靠颜值镇住南唐的江山。只是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国家的败亡和屈辱的囚徒生涯,而他真正成为一轮日头重新升起,照耀的却是万古的词国江山。
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李煜的名字,似乎在三代人中最简单,姑且将姓徐的两年多尚未记事忽略不计,就是李从嘉—李煜,字重光。李煜生来就有帝王之相,被命名为从嘉,而三个月后南唐的前身徐齐政权成立,他从来无意皇位,却意外登基成为南唐国主,他也期盼着能继续依靠“意外”,光耀南唐,改名为李煜。李从嘉代表他无视权力的幼子的无忧生涯;李煜则代表他拥有权力后的有求有待的人生。
或许我们可以再加上几个参照系来深入理解这位词人:他给自己取了很多号,如“莲峰居士”“钟隐”等,以此表达自己对佛教的信奉和归隐的志趣,这是他的自我认同,他的所有行为逻辑也来自于此。面对权力危险的触角,他一直采取退避躲闪的态度,终日乞求佛祖的庇护,逃避生活中的隐忧。登上王位前如此,兵临城下甚至破国亡家后依旧如此,这种归隐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两首《渔父》词中: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李煜的作品真挚自然,往往倾向于直抒胸臆,对权利的淡漠又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几分洒脱自由的况味。李煜的幸与不幸在后人看来都有些传奇的色彩,似乎仅仅依靠生有异表,不必努力就获得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他也寄希望可以这样守住自己的国家,直到不得不面对国破家亡。
亡国之后,他肉坦出降,被宋太祖封为“违命侯”,赵匡胤也没有想到,这个一直选择退让的南唐政权坚守到了最后一刻,所以给了他一个屈辱的封号“违命侯”,说他“违命”,自然是不听话,伴随着这个封号而来的,是全方位屈辱的囚徒生涯。而南唐国破,他又被后人称为李后主。毕竟当一个国家灭亡了,“吉祥物”还能有优渥的生活吗?他将要面临的自然是物质的困窘和精神的屈辱、践踏,最终李煜在残忍的虐杀里告别人世。亡国后,“违命侯”是他的现实敌人给他的屈辱封号,李后主则是后人对他政治身份的总结。
当李煜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他将这种痛苦直抒胸臆地写入词中,他的名字就伴随着一种新兴文体词冉冉升起,并且熠熠生辉,万古长明,后世论者纷纷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甚至一致尊他为“千古词帝”。只要讲到词,没有人能避开这个闪闪发光的人。在文学领域,“千古词帝”是后人颁发给他的永久勋章。
日边清梦断
被认为婉约正宗的著名词人秦观有一句词说“日边清梦断”,本意当然是日光惊扰美梦,比喻自己美好的愿望、理想在现实中碎裂,不是在写南唐君主,但是我却在整理这部分资料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句词:三代君主为“靠近太阳”而改名,何尝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日边清梦”。而把成为太阳的春秋大梦写入三代人的名字,成为标签,让千年后的我们看见,最终也没有逃脱“断”的结局,不由得让我们“事后诸葛亮”地想:这场关于终极权力的期许终究是个白日梦,早已被大浪淘尽、雨打风吹去,不朽的反而是在文学史上,南唐二主词中李璟的委婉心事和李煜在最屈辱的生涯中的血泪文字,凡此种种,都被后世读者反复咀嚼,乃至千古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