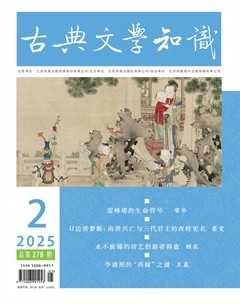作为一种传自印度的建筑形态,塔,历经千年的传承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体系。遍布中国的佛塔不胜枚举,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一座坐落于西子湖畔的千古名塔—雷峰塔。和其他象征生殖崇拜的佛塔有所不同,雷峰塔呈示出的是与西湖气韵相应和的阴柔特质。
雷峰塔始建于风云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为当时吴越的最高统治者钱俶所建。在吴越诸王中,钱俶奉佛最为虔诚,他曾制八万四千座铜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了数百座寺院,为了搜集散佚的佛教经卷,甚至不惜重金派人前往高丽、日本等国,“每遣使修贡,必罗列于庭,焚香再拜,其恭谨如此”。钱俶的崇佛之举让江南的佛教文化得以兴盛,而其崇佛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修建雷峰塔。史载,这位笃信佛教的统治者最初将雷峰塔高高矗立在西湖南岸的夕照山上时,曾将其命名为“黄妃塔”,这是因为他有一位十分宠爱的黄姓妃子,这位黄妃温柔贤惠,知书达礼,彼时,刚刚生一男婴,钱俶欣喜之余,为感念佛恩,遂命工匠建造了这座佛塔。据说原计划要建千尺十三层,后因财力有限,实际施工时只建了七层。尽管塔的高度减了,但钱俶对佛的虔诚却一分都不能减,在其手书的《华严经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凡于万几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盖有深旨焉。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瑶具,创窣堵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塔成之日,又镌《华严》诸经,围绕八面,真成不思议劫数大精进幢。于是合十指爪以赞叹之。塔曰“黄妃”云。
当重檐飞栋的雷峰塔被冠以“黄妃”这个名字,并与佛陀的庄严法相一起构成吴越特有的神圣时,这座塔就已经与西湖水实现了一种阴柔的契合。雷峰塔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周身弥漫的是一份柔美的女性气韵。
黄妃塔前日西沉,采菱日日过湖阴。
郎心只似菱刺短,妾意恰如湖水深。
—释福报《竹枝词》
元代僧人福报的这首《竹枝词》,道出了“黄妃塔”与西湖水的相映成趣,也指明了“黄妃塔”与生俱来的阴柔特质。和这位避世佛门却心向风月的僧人一样,同时代的元人钱惟善也喜欢将夕照山上的雷峰塔称为“黄妃塔”,这位结庐于钱塘江畔五云山下的杭州诗人,曾于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和友人一起登临雷峰塔,写下了《与袁鹏举钱良贵同登雷峰塔访鲁山文公讲主》一诗:
钱湖门外黄妃塔,犹有前朝进士题。
一字排空晴见雁,千峰照水夜然犀。
周遭地带江湖胜,孤绝山同树木低。
二客共驰千里日,故乡各在浙东西。
很可能是吴越国君钱俶后裔的钱惟善在这首诗里直呼雷峰塔为“黄妃塔”,一是体现出对雷峰塔民间称呼的认同,另一层意思好像也在有意彰显自己作为钱氏后人对古塔身世的更多了解。一座“黄妃塔”,已然成为这位钱塘隐士傲然于物的精神寄寓。尽管雷峰塔的别称除了有“黄妃塔”外,还有叫“皇妃塔”的,背后的故事与传说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雷峰塔从高高矗立在西湖之畔的夕照山上时起,就已经和一位夹藏进历史卷册中的女人紧紧地绑在一起。碧波荡漾的西湖水,在用一层层的涟漪放大雷峰塔倒影的同时,也将一个吴越女子的身姿融进了深深的湖水之中。
当然,就像钱惟善在诗中有意将西湖说成是“钱湖”一样,雷峰塔和西湖都是让他引以为傲的底气。这种底气的来源,正是钱惟善祖先所创建的吴越国。吴越国的第三代国君也是末代国君钱俶,肇建的雷峰塔不仅是一座昭彰着自己宠妃的名字、高标崚嶒的佛教景观,更是其“示弱”政治的物化呈现。
早在吴越建国之初,钱俶的祖父钱镠就将“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定为国策,这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乱世武人,虽偏居东南一隅,却坚定地认同大一统观念,与此同时,“稍有余暇,温理《春秋》,兼读《武经》”,对宗室子弟进行儒学教育,教导他们要“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临终时,更是叮嘱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此后,历代吴越国君无一人敢违抗这条祖训,一直都外示柔服,对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对于钱氏的柔服政策,苏轼曾评道:“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
这条“示弱”的祖训传到了钱俶时代,体现得就更加明显。笃信佛教的钱俶在治理吴越期间,不仅大修寺庙,同时也将“慈悲寡欲”“众善奉行”的佛教思想融入治国理政之中。走进七十余载吴越春秋,我们看到的是三任国君“每岁租赋逋者悉蠲之,仍岁著为令”的宽以待民,是“境内大旱,边民有鬻男女者,命出粟帛赎之,归其父母,仍令所在开仓赈恤”的温和持中,尤其是第三任国君钱俶,更是将佛教教义与“纳土归宋”实现了契合。在宋廷攻打南唐时,南唐后主李煜曾以唇亡齿寒之喻求当时的吴越国君钱俶出兵相救。而钱俶却颇识时务,认定北宋统一的局面乃是大势所趋,不仅没有出兵相助,反而亲率五万大军攻下了南唐的常州。此后不久,更是在“天竺大士”的“神启”下做出决定,史载,“忠懿王(钱俶)将内附,决于天竺大士,梦大士以彩绳围绕其宅,归宋之意始定”,决意“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了中央政权。对于钱俶此举,后世一些人认为其应据守吴越之地,拼死力战,实在不该拱手降服;然而,站在更加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我们应当用一种开放的历史观来看待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事实上,钱俶的这种“示弱”,对于吴越子民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福祉:“以纸为甲,以农为兵”的南唐“白甲军”,最终被宋军打得一败涂地,昔日“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金陵城在历经惨烈屠戮之后,已经是满目疮痍;而与之相反,受益于和平统一,吴越都城杭州的百姓却免遭涂炭,归宋之后,杭州更是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繁荣期,呈现出“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柳永语)的盛景。而在纳表归宋之后,钱氏后人也享受到了五代十国王孙后裔中的最高礼遇,三千钱氏族人,皆“文武自择其官”,到了北宋末年,生活在开封的钱氏后裔已达上万人。
塔轮分断雨,倒霞影、漾新晴。看满鉴春红,轻桡占岸,叠鼓收声。帘旌。半钩待燕,料香浓、径远趱蜂程。芳陌人扶醉玉,路旁懒拾遗簪。
郊坰。未厌游情。云暮合、谩销凝。想罢歌停舞,烟花露柳,都付栖莺。重闉。已催凤钥,正钿车、绣勒入争门。银烛擎花夜暖,禁街淡月黄昏。
—周密《木兰花慢》
生活于宋元之际的文人周密,曾于某个暮色四合的黄昏,登上夕照山,站在雷峰塔下,吟诵起这首《木兰花慢》。彼时,和前面提到的僧人福报、隐士钱惟善一样,这位南宋遗民所看到的雷峰塔已不是建于三百多年前的雷峰塔。当年钱俶所建的雷峰塔已毁于北宋末年方腊起义所点燃的一把大火,但和中国很多历史文化坐标一样,雷峰塔也在不断重建的过程中延长着自己的“生命”。周密所歌咏的雷峰塔,其实是南宋僧人智友化缘而建,但塔的兴废更替不可能消弭其自身的历史“基因”,我相信,在斑驳的塔身上,敏感的文人周密,一定已经找到了雷峰塔那份特有的阴柔示弱之美。
当然,说到雷峰塔,一个虚化的女性是绝对不能绕开的,她就是妇孺皆知的白娘子。这位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女子,在由妖到人的嬗变中,丰富着雷峰塔柔情似水的女性形象,但同时,也像坚挺的雷峰塔一样,呈示出女性柔弱背后刚烈的一面。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的文本依据,可追溯到唐人传奇《博异志》中收录的一篇异闻,北宋时,它被编入了《太平广记》,到了明代,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文最终成为这个传说最完整、最丰富的版本,家喻户晓,流传至今。自此,西湖的烟雨,断桥的春情,还有这座被法海用来镇妖除魔的雷峰塔,都和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当人们提起雷峰塔,只记住了被镇压在塔下的那条凄美的白蛇,而忘记了它真正的肇建者。但是,也正因如此,雷峰塔的女性气质才得以在中国众多佛塔中独一无二。
由此,1924年9月25日那声从夕照山上传来的轰天巨响,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笔锋犀利的鲁迅在其《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活该。”在鲁迅看来,雷峰塔的象征意义已远远大过景观意义,雷峰塔的倒掉,其实是封建文化的坍塌。而人们也正是在这震耳欲聋的坍塌声里,看到了“柔弱”背后力量的爆发。诚然,雷峰塔的倒掉,主要归因于岁月沧桑、风雨剥蚀,尤其是明末嘉靖年间入侵杭州城的倭寇点燃的那场大火,更是让雷峰塔徒剩砖瓦。但一个戏剧性的原因也不能忽视:由于民间盛传供奉雷峰塔的砖石可以早生贵子,一时间,人们都开始疯狂地盗挖塔砖,而在盗挖的人群中,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女性香客。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座最初以柔弱命名的塔,最终,毁于柔弱。
2002年,在雷峰塔坍塌78年后,一座金碧辉煌的新塔重新矗立在浸满沧桑岁月的塔基之上,这座在中国风景史上创下数个第一的新塔,不仅以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赋予了雷峰塔傲然于世的雄姿,更因其对古塔遗址的创新性的覆盖保护得到了中国文化界的广泛盛誉。当络绎不绝的游人拾级而上,在领略过雕刻细腻的佛教故事、吴越春秋、白蛇传说之后,便可登临塔顶,极目四望,平静的西湖,壮观的灵隐寺,苍翠的飞来峰尽收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