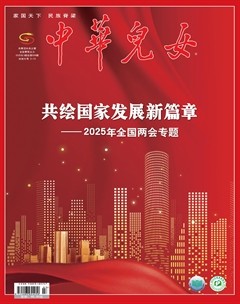阳和启蛰,万物生辉。每年2月,中国科学院华南国家植物园里都宛如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草木葳蕤、花丛锦簇。然而,在这片绚烂的自然美景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却常常步履匆匆,无暇驻足。作为我国植物保护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将心血倾注于科研、管理和履职之中,日程总是紧凑而充实。
任海长期从事植被生态恢复研究和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工作,他带领团队共筛选了200余种乡土植物,研发了集规划、选种、繁殖、栽培、搭配和养护于一体的配套植被生态系统方案,广泛用于海岛、丘陵的生态恢复。在珍稀濒危植物保护方面,他利用生物技术和生态恢复技术集成方法,解决了36种珍稀濒危植物的繁殖问题,助力它们重返自然怀抱,绽放出生命的奇迹。
2022年,华南国家植物园正式挂牌成立。2023年,任海当选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将科研的热情与责任带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其实当代表和搞科研有相似、相通之处,都要勤学习、常调研、多思考,才能接地气,才能发挥作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他充分利用专业优势,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为国家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他还深入人大代表联络站,倾听民众心声。他坦陈:“人大代表是一座桥梁,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他希望将最真实的一线期盼带到全国两会上。
怀揣梦想,探索生态恢复的方法和途径
1970年出生的任海,生长于湖北黄石。在他高中时期,一个清晨6点的广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悄然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广播里经常提到,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也成为我对生命科学最初的兴趣”。
黄石是一个以重工业闻名的城市,电厂、钢厂、煤矿和石灰厂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工业骨架,这些工业活动无疑给周围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任海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每当石灰厂矿山的放炮声响起,灰尘滚滚,而旁边煤矿堆成的煤矸石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荒凉。这些景象都深深地触动了他,让他萌生了用生命科学恢复家乡生态环境的想法。
于是,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任海毅然选择了生物学专业。这个怀揣梦想的青年决心投身于生物学研究,希望用自己的知识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
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后,任海刻苦学习,不断汲取知识,深化对生物学的理解。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后更名为华南植物园)的生态学研究生。从此,他的研究方向从生物学逐渐聚焦到了生态学。
在谈及研究生期间的感受时,任海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生态学领域,但也曾有过困惑,一度为自己无法发表高水平英文论文而苦恼。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努力,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生态恢复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那时,任海经常深入大自然进行观察和实验。刚入学时,他的导师曾要求他认熟500种植物后再回来,通过观察和学习,他逐渐掌握了植物的识别技巧。在野外的学习经历不仅让他对植物有了深入了解,也让他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珍惜每一次野外调查的机会。
任海曾遍访华南地区的许多原始森林和退化草坡,并将这些地方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原始森林和退化草坡的差异,探索生态恢复的方法和途径。每一次野外调查都让他收获满满,为他的生态学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动力。
“在野外考察中,我们遇到过不少危险和有趣的事。比如,在暴雨中躲避洪水,爬到树上避险;在山上做实验时,要时刻警惕落石和滑坡;遇到蛇、蚂蟥和马蜂也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热爱这份工作,因为这让我们有机会亲近自然,了解植物的奥秘,抚慰心灵。”任海说。
服务国家,为改善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博士毕业后,任海留在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之后到美国和荷兰学习交流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让他对生态恢复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看到生态恢复学在改善环境、促进生态平衡方面的巨大潜力,也更加坚定了从事这一领域的决心。
任海发现国外学者的科研思维与自己的科研思维存在一些差异,“他们搞科研强调观察、提出科学假设、设计实验验证假设,并最终得出结论。相比之下,我之前的科研思维更偏向于描述性,缺乏深入的科学探究。这种差异让我意识到,科研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
国家的一系列生态保护和恢复工程为任海提供了实践科研理念的机会,他为自己所学能够为国家服务,为改善生态环境贡献力量而感到振奋。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使全国上下都强烈地意识到,加快林草植被建设、改善生态状况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海在植被生态恢复研究和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的道路上,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发现了南亚热带典型人工林下乡土树种定居限制机理及利用护理植物的解除对策,利用生物技术和生态恢复技术集成方法实现了36种珍稀濒危植物野外种群的生态恢复。他先后主持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A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10余项;出版《恢复生态学导论》等专著3本,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SCI论文15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12项。

任海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广东省自然科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成果6项,还获得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广东省第六届五四青年奖章、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等荣誉。他用自己的经历印证了,只要心中有梦,勇于探索,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敢于挑战,攻克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
在植被生态恢复研究中,任海坦言遇到了不少挑战。其中,筛选适宜的乡土植物并研发配套的植被生态系统构建方案,以及将这些适用的技术真正推广到实际应用中,是最为突出的两大难题。
任海介绍,首先,筛选适宜的乡土植物是关键。在退化的生态系统中,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至关重要,它们能够迅速恢复生态,节约资源。然而,市场上常见的苗木种类有限,这些种类虽然种子产量大、栽培技术成熟,但并不一定是最适合当地生态恢复的。相比之下,我国有大量的野生乡土植物资源,但过去很少有人系统研究它们的繁殖栽培技术。因此,如何找到这些乡土植物,并研发出快速规模繁殖技术,让它们能够在恶劣环境下存活,成为一大挑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任海带领团队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科研攻关。通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成功研发出了一系列乡土植物的快速规模化繁殖技术,使得这些植物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且苗木质量高、成本低。同时,他们还研究了这些植物在恶劣环境下的存活技术,确保它们能够在生态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技术上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将这些技术真正推广到实际应用中,又面临着另一大难题——经济和社会问题。生态恢复往往涉及经济行为和社会利益,如果成本过高或社会认可度不高,那么这些技术就很难得到广泛应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注重生态与经济的平衡。在推广技术时,我们充分考虑了成本效益和社会需求,努力让农民和相关部门看到生态恢复带来的实际利益。同时,我们还积极与政府、企业等合作,共同推动生态恢复项目的实施。”任海说。

谈到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工作,任海介绍,我国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高等植物种类多达3.8万种,其中约15%的植物正面临濒危的威胁,“这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并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珍稀植物”。
通过初步分析五六百种珍稀濒危植物,任海发现它们濒危的原因多种多样,人为干扰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如砍伐、过度采集和环境污染。这些行为破坏了植物的自然生境,导致它们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减或恶化。此外,自然干扰,如干旱和洪水,也对植物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植物自身存在繁殖障碍,难以自然繁衍后代。
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的保护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任海带领团队决定采用生物技术和生态恢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为这些珍稀濒危植物找到新的生存之路。在生物技术方面,他们利用组织培养技术,从野外残存的个体上采集枝条或种子,进行快速繁殖。这种方式不仅避免了野外采集对植物的进一步破坏,还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后代,为植物的种群恢复提供了有力支持。
但是,仅有大量的种苗并不足以保证植物的生存,还需要解决它们在野外存活的问题。因此,他们结合生态恢复技术为这些植物创造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即利用先锋植物改良环境,再引入珍稀植物,为解决珍稀濒危植物存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地将报春苣苔、杜鹃红山茶、猪血木等36种珍稀濒危植物进行了回归种植,并产生了后代。然而,回归成功的标准不仅是种植成活,更重要的是能够自然繁衍后代。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对这些植物进行长期的监测和保护。”任海感慨道,“保护珍稀濒危植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有些乔木可能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开花结果,因此我们的工作需要持续多年才能看到成效。但即使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依然坚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这些珍稀濒危植物找到回归自然之路”。
勇挑重担,建设世界一流植物园
2003年7月,年仅33岁的任海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担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党委副书记,后任党委书记,2015年又担任主任。此外,他还兼任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董事会董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植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他介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为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由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院士创建于1929年。如今,全园由三个园区组成。一是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科学研究园区,占地36.8公顷,拥有植物科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农业与生物技术三个研究中心,以及馆藏标本120余万份的植物标本馆、图书馆、《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及Biological Diversity编辑部、信息中心、CMA及CNAS双资质认证的公共实验室等支撑系统。二是紧邻科学研究园区的植物迁地保护园区,占地282.5公顷,建有展览温室群景区、龙洞琪林景区、珍稀植物繁育中心,以及木兰园、棕榈园、姜园等38个专类园区,迁地保育植物20167种。三是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树木园,占地面积约1133公顷,是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我国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共有高等植物2291种,其中就地保护的野生高等植物1778种、引种栽培植物513种。
任海深知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在谈到关于华南植物园的发展规划时,他表示,“我们基于‘四个面向’的定位,即面向国际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希望在植物学、生态学和农业科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华南植物园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植物园。同时,我们也将积极参与广东生态建设,为打造更加美丽、绿色、和谐的广东贡献我们的力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华南植物园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布局和调整。首先,将原有40多个研究方向集中在9个方面,涵盖三个核心领域:植被生态系统恢复、植物多样性形成机制与保护,以及南方特色植物资源的产业化利用。这样有助于更深入地开展研究,提高科研效率。其次,组建大型科研团队,并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同时注重通过发展学科来促进更多学科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实现“任务带学科、学科促任务”的双重驱动。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积极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吸引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此外,关注新兴的前沿方向和未来的技术,如智能植物管理等,努力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
任海进一步表示,华南植物园“十四五”使命定位是,立足华南,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在植物学、生态学、农业科学、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关键技术等方面建成国际高水平研究机构,引领和带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与世界植物园发展,为绿色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积极履职,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海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提案,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任海提交了“关于支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构建,提出重点保护植物类群,并制定行业标准,在规划编制、政策制定、项目投资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服务”。该建议获得国家林草局等部门的积极回复,促进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工作。
当年9月,《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印发,确定在已设立2个国家植物园的基础上,到2025年前将建设5个左右的国家植物园,到2035年前将建设10个左右的国家植物园,逐步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目前,已从全国200多个植物园中筛选出14个候选单位。其中,国家植物园考核评价标准的编制工作正是由任海牵头负责。
“在这个文件里面,我所提的建议大部分内容均被采纳了,我感到特别高兴。”任海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还提到,“以华南植物园为例,自挂牌为国家植物园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物种数量从1.7万左右增加至2万种(含种以下单元),极大地丰富了植物资源,同时承担国家重大重点任务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游客数量增加了一倍。未来,中国国家植物园建设应对标国际知名的国家植物园,以国家使命为导向,以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为核心,坚持国家代表性、科学系统性、社会公益性,有机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讲好中国植物故事,为遏制植物多样性丧失和修复退化生态系统提供有力支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创新方案”。
在2024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任海提出了“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内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重叠问题的建议”,提出“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确保了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历史原因,在国家公园和各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有重叠且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建议保留在自然保护地内的‘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高质量耕地,不改变其生产空间属性,不调出自然保护地”。
这份建议得到了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的关注。自然资源部正在组织起草《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及保护成效评估技术指南》,已考虑将生态保护红线周边一定区域纳入监测范围,探索将生态保护红线周边的零星破碎的永久基本农田“天窗”适度整治、集中、优化,将新产生的生态空间按程序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
今年,任海将拟提一份“关于理顺动物迁地保护管理体系并建设国家动物园体系的建议”。他说:“我国气候和生物地理区域多样,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主要通过自然保护地就地保护与城市动物园、野生动物园、水族馆(海洋馆)和繁育基地等迁地保护方式进行保护。基于设立国家植物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经验,为明确我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实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目标,解决现阶段野生动物保护难题,建议先理顺动物迁地保护管理体系,再建设国家动物园体系。”
任海表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形势依然严峻,动物园迁地保护任务艰巨,我国动物园与世界上先进的动物园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建设国家动物园不仅是推进系统化、体系化动物保护的关键,也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保护的必由之路。通过创新集约社会资源、促进科研成果应用及动员社会参与保护,促进动物园行业树立标准,实现更加系统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建设。
在任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科学家的执着与担当,一位管理者的睿智与勇气,一位人大代表的责任与使命。任海对青年一代更是寄予期望,他鼓励青年们将个人的崇高理想融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在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实践中,确立自己的“生态位”,勇敢发光发热,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 赵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