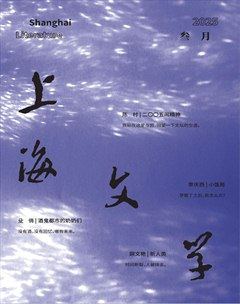一
我读马原新写的小说《动物之山》,但这是小说吗?我边读边质疑,我是带着质疑读完小说的。读完了更觉得它不像小说。但很快我就想通了,马原写的小说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一直不就是这样在写小说吗?四十多年前,一个叫马原的青年写了一篇小说《拉萨河女神》,人们读了之后同样也产生了“这是小说吗”的质疑。看来马原还是原来的马原,他从来就是不按小说应有的样子来写小说!
因为这个原因,马原从他写小说起就被称作先锋作家。马原开始写小说是在一九八○年代,那时候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清楚,那时的小说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本来是外国的,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家们拿过来了,讲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故事,很受读者欢迎。后来中国的评论家(主要是有权力的评论家)给现实主义戴上了各种帽子,比如叫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戴着帽子的现实主义其实也就是给作家的写作设定了更多的框框,作家发挥艺术想象力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新时期开始,文学获得解放,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参与到全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思想斗争中,但他们的“拨乱反正”叙事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他们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竟让当时的文学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从这个角度说,那一代的作家真不简单!但是作家们也深感这种小说的样式对于写作来说束缚力太大,他们按照这种样式写小说,写出来的小说越来越大同小异。这时候几个年轻人站出来了,他们发现了有另外一种小说样式,他们按照这种小说样式来写小说。他们所发现的小说样式也就是现代派小说,现代派小说是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理论基础而重新设计的小说样式。现代派小说虽然在国外已经普及化了,但它刚刚译介到中国,人们没见过这样的小说,有的直呼看不懂,有的则惊喜地说太新奇!让人更惊异的是竟然还有中国自己的作家也按照这种小说样式写小说。也有几位评论家为这几个年轻人所写的小说大声叫好,并将他们的行为称为先锋文学潮。马原就是这几位年轻人中的一员,他写了《拉萨河女神》之后,又写了《冈底斯的诱惑》,评论家发现了马原是把结构主义搬到了小说叙述之中,他把故事结构分解重组,时空关系也不断跳跃,人们也不知道他所讲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和地方,他把人们引到一个结构的迷宫里,让你在迷宫里产生错觉。有评论家将马原的这套写小说的方法称为“叙述圈套”。
马原对于玩叙述圈套的游戏乐此不疲。这一次他写《动物之山》同样是给读者设置的一个叙述圈套。也就是说,他对于要在小说中为我们讲述什么内容并不怎么在意,他或许想到了哪里就讲到哪里,但他对于怎么讲述是非常在意的。显然我们不能像读一篇中规中矩的小说那样,在阅读时能够对小说的叙述有所期待。如果你抱着阅读期待来读马原的《动物之山》,恐怕所有的阅读期待都将落空。我读到第一节“马老师加入”,以为马原是要讲述一个探险的故事,马老师、别样吾、贝玛三个人相约一起去钻一个山洞,山洞外是一个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他们就为什么不能与动物进行语言交流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当他们一致得出结论要为自己没有变成天神而庆幸时,所有的动物都一齐看向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不是很庆幸呀?”这句话仿佛是起跑线上发令员发出的一声枪响,三个人物接下来应该朝着预定的目标飞速跑去呀!但是,对不起,马原转身就让这些人物干别的事情去了。这无足为怪,马原从来就是这样,当小说发生了变化,变出了新的小说样子,他照样也不按新的小说样子来写。马原的文学性格里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颠覆性。可以说,颠覆成为了他写小说的主要方式。
不妨说说这篇小说里的颠覆性。首先完全颠覆了小说叙述的基本逻辑。马原用了一个探险小说的开头,似乎要把读者引向一个神秘之地,但这个神秘之地的探险却在所有动物异口同声的一句话中匆匆收场了。如果说这是马原对小说叙述基本逻辑的一次颠覆的话,那么,这样的颠覆其实非常有价值。他虽然关闭了野生动物乐园这一神秘之地的大门,但他开启了另一扇神秘之地的大门,这个神秘之地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是存在于语言文字的世界里的,这就是童话的神秘之地。
马原这回认真给我们讲童话。这些童话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他讲了很多童话,但他并不去给叙述搭建起一个结构,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他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讲下来,至于第二个为什么要接着第一个,我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但是当你读完了全部的童话后,你再仔细想想,也许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马原式的叙述逻辑。既然是以马原式的叙述逻辑来讲述,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构童话,然后再重述童话,这些童话表面上看还是原初的形态,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许可以说,这些童话是少数民族与马原联姻后的结果。他在文体上进行了颠覆,在童话的叙事中插入大量的议论。在观念上也进行了颠覆。比如在“苍蝇与蛇”这篇童话里,特意将童话的含义往好人还是坏人的方向上引,认为这是讲了一个坏人得逞的故事。
虽然马原热衷于做颠覆性的事情,但不要因此就将马原视为一个破坏分子。颠覆的作用就是破坏,这不假,然而颠覆的目的是为了重建。马原在这篇小说中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的颠覆,而且还在颠覆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的重建。马原是如何重建的更值得关注。请注意三个出场的人物,一个是马老师(分明是以自己为原型的),一个是九十九岁高龄的别样吾,一个是年轻的布朗族女子贝玛。贝玛能够往返于人间和冥界,别样吾嘴里装着一个童话世界,他们两人各自都有数不清的关于动物的故事,贝玛的故事是从现实(包括人间和冥界)中获得的,别样吾的故事是装在自己嘴里的。这两个特别的人要带马老师去看南糯山的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