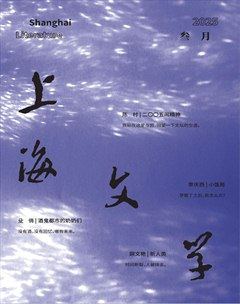棉棉:听说前阵子在柏林的时候,你是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一直待着写作的,是这样的吗?我现在一般都是在早上醒来的那点时间思考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写一点点什么(涂上手霜),有时是很重要的一封信,有时是一篇稿子(虽然我一年也写不了几篇),有时是改小说(它们通常是以前写过的小说的拼贴),可以是任何跟文字有关的东西,有时是回微信,说到这,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习惯于不回微信了……它充分说明了当代生活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文明,尽管我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但我依然坚持在早上回那些需要动脑筋的信息……
大湾:除了待在屋子里写作,现在的柏林可以提供的真的很少。在这里生活十几年后离开然后再回到这里,以为会有新的感受,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柏林对于很多游客来说,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但我算不上游客,我不喜欢现在的氛围。柏林变得昂贵,这种贵不是相对的,就像洛阳的胡辣汤卖三十五块钱一碗。尽管贵不贵和我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可以以低廉的成本活着。所以,在屋子里写作,不写的话待着,这不就是成本极低的生活吗?饭一天吃一顿,喝点咖啡和水(水没涨价,还是六毛多一瓶吧),足够了。柏林除了土耳其人和黎巴嫩人的馆子,再加上两三家意大利菜,没有值得你特意去一趟的饭店。印度菜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哪个国家都是。虽然德国的印度菜和英国的没法比,但是也比柏林的中餐馆或者法餐强得不止一星半点。
写作是件很愉快的事,愉快的点在于你可以随时停止。甚至抱有目的的写作都可以是愉快的,因为你还是可以随时停笔。写不下去放弃了,读着之前已经写的,可能会略感惋惜。如果可以,你再回去接着写,尽管这样对于我来说有点难。我现在还有几个开了头没写完的小说,放着,估计大概率不会完成了。有目的的写作,比如说写“命题作文”之类的,有点像给人写剧本。听别人的故事,写别人的故事,让别人满意。构思这种东西的时候,技巧很重要。你可以认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能得到认可,也会得到回报,经济上的,名誉上的。最终的话语权不在你手上,在导演或者制片人那里。这样的写作是不是文学?不好说,应该不是吧?写作就是写作,文学就是文学,也行吧?
写作是个人状态的一种整理,生活没有什么选项的时候我就会寄希望于写作带来新的选择。我写作的前提是减少一切“没用”的虚妄,把生存条件和欲望降低到最基本,没有了欲望给你带来的困扰,也不会有太多所谓的麻烦找上你,也没有借口了,“我还要处理这个处理那个问题”。人们都太想解决问题了,抱着必死的信念也要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也要试图解决,一直到死。也许停下来问问自己,到底问题是不是问题,要不要去面对或者解决?但是人怎么可能停下来呢,不可能。
棉棉:你这么说让我想起我们在谈论的事情,一对年轻的夫妻,相爱了几年,太太提出离婚,而丈夫不同意,他们一直在微信里沟通,太太着急地给丈夫寄离婚协议和丈夫的东西,可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丈夫就不去到太太的身边,面对面地把太太“争取回来”呢?
大湾:向那些对故事有这般期待的读者感到抱歉,故事有没有着落点不是我决定的,是故事本身。我想先提一个问题,控制和失控(允许失控)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控制?也许这个男人心里有一种难以启齿的隐痛,他害怕那种当面时的沉默、争吵或者不可挽回的决裂,使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有时候,人们宁愿不去直视彼此,也不想被对方看穿或者揭穿对方——那一刻的脆弱、无措和尴尬,比离婚这个社会定义还更让人无地自容。他可能觉得,保持一个隔膜、一道缝隙,可以让自己在想象中继续调适,而不必强硬地将内心的防线拆解给对方看。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乎对方,或对离婚毫无知觉,反倒是因为离婚已经将双方推入一个陌生、难以言说的新关系状态中。他或许觉得,哪怕不见面,都比当面相对时那种无所遁形的真实来得更容易一点。也许想说的并不是离婚,可能更是一种不想结束的状态。不结束便没有新的可能,结束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可能?还是控制和失控的选择,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想延续下去,不想结束。
我也为我的解释感到抱歉。我认为“落点”或者“非常明确的落点”是对小说和文学最大的诋毁。
棉棉:你的电影和小说,往往都是通过一个布局精密但结局“无着落”的黑色故事,表达一种专属于你的混合着疑惑、纯真、两难、爱恨分不清的孤独,你的技术漂亮和精准,冷调而细腻,我在ChatGPT上输入了你的小说《伊维萨岛上的爬行动物》的一个段落,我让Ta分析一下你的写作风格,Ta是这么回答的——
这段文字展示了作者的细腻和略带冷调的叙述风格,勾勒出一种平淡却充满隐秘张力的氛围。作者的写作节奏缓慢,每个细小的动作和感官细节都被细致描述,例如“木帘慢慢升起”“紧接着是一连串闷雷”,这种细致的描写营造了平静、日常的氛围,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生活的无力和困顿。暗含孤独感与无所适从,主人公没有明确的目标或归属感。搬家、被动接受生活安排(母亲的房子)、打量陌生人等情节,都透出一种疏离感。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带有一种被动的观望态度,甚至对自己生活的未来也仅是模糊地思考,缺乏实际的规划或动机。表面平静的文字中透出潜在的紧张情绪。闪电、雷声、突然卡住的面包,甚至不认识的男人在视野中的出现,都似乎暗示着某种不安,或是日常生活下难以解脱的压抑。主人公内心的孤寂感非常明显,不仅与陌生人保持距离,甚至连他母亲都只通过一张纸条来传递关心,自言自语的片段进一步表现出这种内心的孤独。作者在文字中不动声色地表现出人与环境、人与他人间的隔阂。看似平静的日常中加入了荒诞的细节,例如面包卡在喉咙、吐出在咖啡杯里,这些微妙的幽默感使文字更具张力,并透出一种生活的无奈和滑稽感。
前几天,有一天我起得非常早,天还是黑的,我很喜欢加德满都的冬天,它有着冬天该有的魅力,但却没有那么冷,加德满都是一个多种文化、多种时间、多种政治混合的地方,并因此而充满活力,它的底色是放松的,混乱中有一种缓慢的有序,阳光很强烈,并且到处在反光。我租的这间公寓是博大哈佛塔这边罕见的有电梯的公寓,我的窗前是雪谦寺,经常有各种飞鸟和飞机飞过,声音很大,我经常在微信里跟人说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会感叹:我这里经常有很大声的飞机飞过的声音。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是很合适我的。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住过几年很高的楼层,那时也有一种感觉像是住在了飞机场,阳台的落地窗经常会因为没有关紧而有风声……大概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开始关注窗前的景色,我在东大名路八百八十八号住了近十年,我的窗前是北外滩的码头、黄浦江、以及江面上的各种船只,它们大多闪着各种广告灯箱,但在十一点以后,江面是黑色的,会有一些黑色的船在静静地缓慢地移动……现在我会问自己,此时我也是把窗外的寺庙作为一种景观吗?说回现在,那天我起得很早,收到英国导演Michael Winterbottom的邮件,他说我的新书《来自香海的女人》中有一条叙事线是本世纪初的上海,那些party流水账激起了他强烈的怀旧感,他问如今在上海拍本世纪初的上海是否有可能……
大湾:我挺好奇的,冬天的加德满都是怎么个冷法?上海的那种湿冷,还是北方的干冷?屋子里有暖气吗?那里冬天有没有特殊的味道?比如说在北京或者北方,空气里有烧煤的味道,出租车里有人身上的油脂臭,饭馆里有油烟味儿……
飞机飞过哪里都会留下巨大的躁动,巨响和震动。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你总能看见一个个小光点在半空中排队,起初我以为我看见了奇景异象,后来我以为是UFO,再后来才明白是等待降落的飞机,和很多即将抵达目的地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