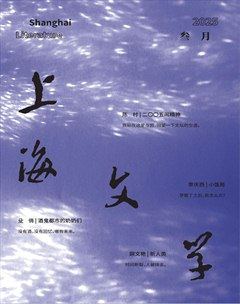1
面对一座建筑时,我们不光希望它具有离学校、医院和超市近的功能,还希望它有一个一眼就能让人记住的外观,以及能满足人们多变心情的附属设施,比如水池、大面积的绿色植物以及适合孩子玩耍的小广场。
在一家五口已经没办法挤在一套只有九十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这个现实出现后,我们就是按照以上标准,开始关注并且最终购买了城南这处新建小区里的房子。
它还只是图纸上的设计时,我就开始了解它。在售楼大厅,妆容精致的售楼小姐指着沙盘上的模型建筑,对整个小区展开讲述,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或者说她已经对参观者的心理了如指掌,每一个细节,都能解决我对未来可能会居住的小区的困惑,甚至不需要我去咨询,她就准确地说出了某些问题的答案。
在她嘴里,一座建筑已经不是石头、钢铁、水泥、木头与玻璃的排列组合那么简单,而是拥有了审美、判断力以及地位等等综合因素。出于对文字的敏感,我掌握了她话术中的一些技巧:只要小区边有一条街道,不管是主干道还是背街小巷,都可尊享一站式抵达的城市交通路网的便利;如若靠近公园的话,就是出门即可享受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而离此处稍远的湖泊和医院,被说成靠近优质医疗资源,零距离享受亲水带来的优雅与从容。
对于房子内部的介绍,话术再一次让我领略了词语的精妙:以匠心的建造回馈客户,用精美的设计给每一间住宅都赋予新的生命力,低密度的格局,奢华的豪宅装饰,充分彰显典雅大气的风范。这句话被说出口的时候,我有些恍惚,就觉得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和标准的样板间是如此匹配。此时,建筑的审美和其他价值,已经变成了单一的实用性;此时,沙发恰到好处,对面的电视也是;阳台恰到好处,远处的风景也是;灶台恰到好处,整个厨房也是……以此类推,一切都恰到好处,就缺一份购房合同,然后你就拥有了恰到好处的一切。
精致的沙盘,精致的妆容,加上精致的推介词,让我有一种已经和面前这座即将动工的小区之间有了关联的错觉,内心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拿下它的冲动。对于这种心情,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了不曾见面而经由媒妁之言促成的婚姻,充满期待,也充满风险。
在持久的关注和多重的作用之下,我似乎对这个小区的每一个细节有了一定的了解,又似乎说起任何细节都语焉不详,可是这种矛盾的心理,竟然没有影响我要在这里买房子的决心。而在看到这个区域要建一座图书馆之后,我更加笃定,这里将是我未来几十年的安身之所。于是,开始借钱、排号、抢房、贷款,然后就是漫长地等待。每个月四千多元的房贷提醒我,我要为这套位于十八层建筑第四层、套内面积一百三十多平方米、采光一般、位置一般的房子买单三十年,这真是一场漫长的消耗和博弈。
拿到钥匙的那一刻,我内心很平静,竟然没有欣喜,而是有一种被自己绑架的感觉。在办税大厅排号等待缴税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选择这里安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可是诸多问题却又涌上心头:我真的需要买这里的房子吗?同事说以同样的价格,完全可以在靠近优质学区的地方买更大面积的房子,我为何要如此固执?难道仅仅是因为售楼小姐的精致推销,或者是图书馆的吸引?这些问题注定没有答案。唯一明确的是,从拿到钥匙开始,我要为这套房子开始焦虑,开始忙碌,开始新一轮的债务偿还。
2
趁着“十一”长假,这套新房子进入了装修季。其实我们并不着急搬家,只是想尽早看到它能居住时的样子,这样也好利用北方新的供暖季对它进行一次彻底的晾干。
整个装修的关键人物姓马,是一个头发乱糟糟,看上去像韩国某个电影明星的乡下人。他说话含糊不清,带着浓重的方言味,但是并不影响装修品质。他最喜欢说的是,你放心,我干装修二十年了,对这一行清楚得很。
这一点我是真放心的,不光是因为他给我同事以及同事的亲戚装修的几套房子效果都很不错,还有一点至关重要:我第一次带他去看房子,连个卷尺都不带的马师傅,竟然就能判断出房屋的宽窄高低,并且迅速计算出需要多少块瓷砖,需要多少板材,以及需要多少插座和开关。
在同行看来必备的技能,成了我选他的决定性因素。简单地约定了一些内容之后,装修约定就算正式达成了:装修性质为全包,软装的所有材料和劳动力全部由施工方负责,我只需要对材料的品牌和颜色进行选择即可。
没有刻意选开工的日子,一个周天的上午,我领着马师傅和两个工人进入了场地。一进门,他们三个就开始换工装,很快就默契地出现在了自己的工位上。一瞬间,整个屋子里就奏起了电钻、锤子和切割机的交响曲。
我观察了一下,他们所谓的工服,无非是一些沾着水泥和尘土的脏衣服,并不是专业装修队伍那样整齐的制服,不过,这身衣服看上去比进门前穿的那身要得体,并且更能代表他们。他们三个再也没有理我,一个专心砸墙,一个蹲在地上切割着墙砖,另一个迅速地处理着地面上的杂物。
我从屋子里退出来之前,把一把钥匙递给了马师傅,彻底把这里交给了他们。随后的日子,我和马师傅的联系基本上就靠电话了,不管我要跟他说什么问题,他总是一种让人很放心的感觉。也确实如此,一个在装修市场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装修工,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问题没遇到过,什么人没接触过。
这也可能是他在和我交流的过程中,从来不谦卑逢迎的原因。他给我打电话,从来不称呼我的姓名,我怀疑他压根儿就没记住我姓啥,更别说我叫啥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事都在马师傅的掌握之中,装修开始前交代过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只有需要业主出面协调或者需要询问我的意见的事情,他才会打一个电话。并且,电话内容会简单到:窗子是半包还是全包,或者没电了你处理下之类的句子,没有问候语,也没结束语,句子直截了当得像他砸到墙上的锤子发出来的声音。
装修进入到第五天,刚好是一个周末,我专门去看了装修现场。房子已经面目全非,阳台内层的窗户,变成了废铁框和一堆玻璃碎渣。早晨,阳光越过正源街,还没被对面的建筑挡住之前,落进还没有安装外窗户的房子里,屋内的墙壁就涂上了一层浅黄,杂乱的地面,和白色的墙,被晒得暖洋洋的。
马师傅正在用切割机对整块的瓷砖进行分割,钢铁的薄片在电动马达的作用下,深入瓷砖内部,火星和灰尘很快就包围了正在切割瓷砖的人,一粒粒尘埃组成巨大的阴影,在光线的照射下,正在忙碌的那个人,双手收放自如,似乎正应和着一曲华尔兹的节奏起舞。
房子也像是颇为享受这份嘈杂,或许是也在等待着被瓷砖、油漆、木材改变之后的样子。于是,它配合着装修工人,装修工人也像驯服一头猛兽一样,从它的内部拿掉多余的部分,再填补上欠缺的部分,不断地调整之后,毫无用处的室内保温层和门框已经被清空,房子的野性逐渐消失,而带着装修工人痕迹的温顺的性格慢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