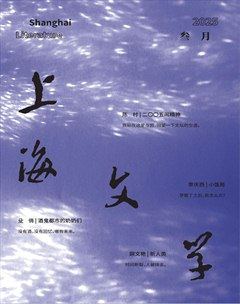打小起,我就一直喜欢在路上行走。有事,或者没事,春夏,或者秋冬,都一样。只要有空,我就会一个人步行上路,开始我的闲逛,或者行走。
喜欢在路上步行,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总是生病,于是母亲就千方百计地鼓励我爱上体育活动,鼓励我到外面去玩。在母亲的鼓励下,有一年夏天,我突然爱上了徒步行走。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每年一到盛夏放暑假的时节,我就开始了徒步行走。一般都是在早饭后,也没有什么事,但有一个具体的地名,吃过早饭,穿个短裤,穿个背心,穿个黄球鞋,却从来不戴帽子,就出门了,走出城市,沿着一条公路,一直往前走。太阳越升越正,一直升到头顶上,阳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像有一盆炭火不断从头顶上往下倾倒,温度越来越高,那时候的空气没有半点污染,因此阳光直射,明亮炫目。我却越走越有劲,天越热,反倒越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走得越坚定,步伐也迈得越有力,人也越兴奋。我走热了,就把背心脱下来,有时顶在头上,有时甩在肩头,用一只手勾着,另一只手甩开大步往前走。那时候的公路以砂石路为主,一路走下来,脚上、腿上白蒙蒙的,都是灰。
起初,我走的路程比较短,早饭后出门,走到北十里,或走到紫芦湖,或走到西十里铺,或走到梅庵子,就返回了;后来我越走越上瘾,越走越带劲,也越走越远,有时候走到离城二十里的朱仙庄,或离城二十多里的西二铺,或离城十五里的桃园集,或与蒙城县交界的一个小集市,或与濉溪县交界的一个小集市。走到那些地方时,天也晌午了,要么在路边的小茶水摊喝一碗梗子茶,和拉架子车在茶摊歇脚的农民说说话,和他们互递一支烟吸(都是从父亲烟盒里偷的),有剩油条就买几根吃,或者在路边小店用一两粮票买一小盒饼干吃,歇够了,再转身顺来路返回城里。这样来回少则三四十里,多则五六十里,傍晚回到家中,虽然腿脚有些酸乏,心灵上却感觉有极大的满足,脚力也变得精健无比,平时如果需要步行几里路,就完全不当作一回事了。
少年时养下的习惯,此后一直延续着,每年一到夏天,心里就痒痒抓抓的,脚步不由自主就往外面走去。一九七八年我上大学,第一年的暑假脚筋发痒,不由自主地走回了泗洪老家,在老家的平原上撒欢、乱跑。第二年的暑假脚筋又痒,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大别山,在大别山里步行到佛子岭、到磨子潭、到大化坪、到青枫岭、到白莲岩、到胡家河、到白马尖。第三年暑假脚筋更痒,不由自主“走”起来,乘火车“走”到了甘肃、青海、宁夏,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和浙江的两个个体牙医作伴,晚上住灰尘很厚的废车厢,白天在高原的道路上步行,碰到少数民族的拖拉机就拦拖拉机走一段,碰到解放军的军车就扒军车行一程,没车就步行,从天棚一直走到天峻县。
后来行走淮河及淮河的支流,也是少年行走的延续。那一次走淮河北岸支流浍河,初夏的早晨从园宅集出发,一路走过浍河水结香涧湖的湿地,只见芦苇紫红色的幼芽正纷纷冒出浅水和湿地,这里一片,那里一汪,这里一片紫云,那里一片红雾,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我望得呆住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芦苇幼芽出生的浩大阵势,我站在湿地边缘,由近至远地看,又由远及近地看,看了许久,我又小心择路走进有干有湿的湿地里,在紫红色的芦苇幼芽的阵仗里穿行,呼吸着带清香味的空气,满目都是植物萌芽的身影、雀鸟飞过的痕迹,满耳都是鸟雀婉转悠远的歌唱,眼见着春天的热气腾腾上升,胸襟里涌满春天催人的鼓动。又一次仲夏走濉河,在灰古东边的河坡上蹲下来看一窝名叫“叫油子”的昆虫从一个土洞里,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陆续钻出来;坐在沙土地上听仲夏的暖风吹动杨树叶哗啦哗啦响,杨树叶被风吹得左右翻动,就像在不知疲倦地展示它叶面的美妙一般。
有两年在北京城里小住,但到了初夏麦熟季节就打熬不住,一定要乘车回到平原上走路看小麦。乘绿皮火车悠然到颍河附近的黄桥,住在一个小旅店里,然后冒着大太阳在黄桥附近的平原上、小河边、麦田里、土路上、荒草间,晒一晒,走一走,才觉得心安了下来,情绪才稳定下来。经过黄桥火车站时,请道口工人帮忙拍了张照片,洗出来后吓了一跳,虽然我皮肤较黑,但那张照片中的我,脸被夏天的阳光浆得发亮,那笑容是发自内里的健康和开心。合肥的盛夏时节我会乘车到一个叫新仓的小镇去,盛夏的正午,三四十度的高温,空气灼人,街上、村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待在外面,这正是我独霸天地的好时机。我穿着长裤、T恤、皮鞋,迈开脚步,从小镇东边走到河堤上,然后沿着河堤一路向东走。一般而言,我都是全神贯注地走,但周围的地形、风物、村庄、人迹,也全会被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我在高温酷暑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向前方我并不知晓的地方,那时只是想,不论走到哪里,只管一直沿着河堤往前走就可以了,无论走到哪里。
正由于我少年时期总是在盛夏时节外出活动,钓黄鳝、步行、游泳,因此我从来不怕夏天,不怕热辣辣的阳光,不怕太阳的暴晒,反而对夏天特别来感觉。盛夏野外的热空气,盛夏河边烫人的沙土地,盛夏河面上炫目的波纹,盛夏田野里绵软的作物叶片,盛夏野外的一切,我都觉得特别亲切、熟悉。四十年后有一个盛夏的中午,我开车到城市的一个地方办事,那里有一个巨大而空旷的停车场,酷阳高照,明光晃晃,所有在那里停车的人,下了车都匆忙跑走了,女士则赶紧撑起遮阳伞离去。我下了车,却突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对盛夏阳光的亲切、熟悉和亲近。我锁了车门,在空无一人的巨大的停车场里,沐浴着盛夏正午热辣的阳光,慢慢从停车场的一端,走到停车场的另一端。我去办完事以后,匆忙又回到停车场,又慢慢从停车场的一端,走到停车场的另一端,无比满足地大口呼吸着膨胀灼热的空气,让火热的阳光沐浴我的全身。那真是一种久违的巨大的吸能过程,无与伦比的顶尖的享受!每个人都有他的尖峰时刻,那一刻也正是我的尖峰时刻!
真的要发自内心地感恩妈妈小时候对我的鼓励和引导!母亲对我到处跑着玩、钓黄鳝、戏水游泳、徒步行走,一直是鼓励有加的,她知道这对改变我小时候的体弱多病有太多的好处,其实这是母亲帮助我建立起了我一生得益的一种生活方式。少年时我跑遍了宿县城郊的村村落落,后来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指引下,我又跑遍了淮河流域的河河汊汊,再后来我又情不自禁地跑去了大别山、大西北、秦岭、太行山,跑去了华北平原、青藏高原。我的身体在不断行走和行动中变得健康起来,变得动态平衡了,我的心灵也永远不会死水一潭了,我的思想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变得动态平衡了,起码我知道看事物、看天地、看社会、看人生,都要动态且平衡地去看,不会把它们看成死的,看成一成不变的,看成扭曲的,看成比例失调的。起码我会告诉我自己,前途和风景都只在自己的脚下,只要你走起来,行动起来,就能见到风景和远方,就能找到出路,就能使思路活泛、清晰起来,就有前途、有办法。
我会连续好几天在路上徒步行走。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起《尔雅》记录的各种道路的名称:仅通往一个方向的路才叫“道路”,通往两个方向的路叫“歧旁”,通往三个方向的路叫“剧旁”,通往四个方向的路叫“衢”,通往五个方向的路叫“康”,通往六个方向的路叫“庄”,通往七个方向的路叫“剧骖”,通往八个方向的路叫“崇期”,通往九个方向的路叫“逵”。因此,我们后来才有了“四通八达”“康庄大道”等说法。多日后,当假期用完了,我就该收拾行囊,起身回家了。
以前,夏天,但也可能是其他季节,我会打点一个小书包,小书包里有几件换洗的背心、裤头,一个小水杯,偶尔有几小袋桂圆茶,一两本书,笔和笔记本是必带的,先离开城市,不乘车、船(那时候的中小城市里也没有公交车、船),步行到乡下一个叫麦粒的小镇。在那个小镇上,找一间便宜的旅店住下来。晚餐在镇中一家土菜馆里,要一盘卤猪肚,一碟花生米凉拌萝卜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两只白面馍,二两红芋干子酒,吃饱喝足后,回到房间。房间里没有桌椅,我就跪在床边,把笔记本放在床沿上,记当天的日记和笔记。记完后,我上床看书,困了,就关灯睡觉。天亮后,开始我此后多天的徒步行走。
第一天,我走往正东方向。那里是日启之处。我走去那里看日启。
东五里,那里有一座村庄,村名叫杨树头。我先沿较宽的土路走出小镇,土路两边的行道树都是杨树。天色还很晦暗,小镇和野外的某个村庄里,会传来几声狗叫。看不清脚下土路的野草上有没有白霜,但感觉肯定是有的,因为从鞋外传来一阵阵湿凉的寒气。杨树头村的村东头,果真有更大一片杨树林。杨树林东是一片高荒地。在那里迎着隆冬的寒气站着,手袖在棉袄的袖口里。笼罩在大地上的寒凉气逐渐消散。东天亮了许多。现在,越来越看得清眼界里的事物了。杨树林里头愈益喧闹。各种鸟都在叫。多的是麻雀,还有一些喜鹊,另有一些灰喜鹊。村庄里则是一片鸡鸣声。东稍偏南方向的天际,由灰白而惨白,再由惨白而苍白,又由苍白而脂白,终由脂白而彩白,太阳就从东稍偏南方天际的寒凉之中,冒将出来了。
看完日启,我转过身,踩着尚未融化的白碴碴的寒霜,快步走回杨树头村。我走进村路边一家开着门的农家,走到堂屋里,看那家人和面蒸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