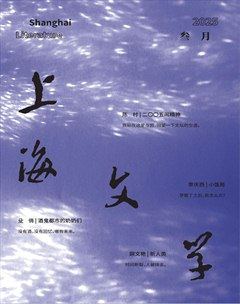一、向书致谢
上小学,听老师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用功读书的故事,有点胆寒,似乎读书是一种刑罚。好在家里拮据,除了课本,没书可读。中国明清四大名著,都是放了学,同学在书摊上租了小人书,我在一边厚着脸皮蹭看的。也就只留下了一些肤浅的印象:《水浒传》我喜欢鲁智深,当提辖扶弱凌强,当和尚见佛杀佛。讨厌宋江,为了当官害死了那么多好汉。同情潘金莲,但凡她有一丁点追求幸福的权利也不至于沦为杀人犯。《三国演义》我喜欢关公,千里走单骑,孤独而豪迈!刘备太装,诸葛亮心眼太多,折寿。曹操会写诗,但不是好东西。杨修喜欢卖弄聪明,倒了血霉。周瑜真帅,女孩子为了让他看一眼,琴都弹不好,可惜气量小。《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和蜘蛛洞是我的少年妄想。唐僧是我本家,但我不喜欢他的一本正经。如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让我从小尽可能远远避开绝对权力。《红楼梦》里女孩多,最可爱是史湘云,傻乎乎的,没心没肺,喝多了酒醉卧花丛。宝钗甜熟乖巧,像女干部。黛玉小性子,谁也受不了。多年后,以写作为职业,接触到中外长篇小说,但我从头到尾读完的只有雨果的《九三年》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读完了,立刻明白我这样的人被喊做“作家”纯粹是一个笑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在陶渊明故里的乡镇务农、工作,算是他的后世同乡。他在自传里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与他有同有不同:同的是“不求甚解”,不同的是不怎么“好读书”。除了忙于生计,跟懒惰、不愿刻苦不无关系。单位分了房子,我十分起劲地做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塞进了一整面墙的书,煞有介事地“坐拥书城”,结果,也就是“坐拥”而已,偶尔翻过几本工具书,借口忙于公务和家务,其他的纹丝未动。将近三十年后,我移居岭南,那些书全数送了亲友。
知道同行中的许多人遍读中外名著,个个成就斐然,很羡慕,但也只能是像唐朝诗人孟浩然写的:徒有羡鱼情。有些年,文坛《红楼梦》热,读《红楼》、说《红楼》、续《红楼》,蔚然成风,我甚茫然,找各种歪理为自己的无知辩解:如果只有读了《红楼梦》才能写好小说,那曹雪芹是读了谁的小说才写出《红楼梦》的呢?参加文学活动,与著名作家刘庆邦同座,我借机请教。他告诉我,他把《红楼梦》仔细读了五遍。惊得我掉下巴。难怪他被称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而我的写作始终原地踏步。
在大学插班学习,一位几乎是晚辈的本科生很怜悯地对我说:你们的出现是得益于历史机遇,缺乏知识根基,走不远的。我一脸通红地认可。
举凡大作家,没有浪得虚名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百分百是个认认真真的人:认认真真读别人的书,认认真真写自己的书,他的《向书致谢》充满激情:
“它们静悄悄立在墙边,仿佛都睡着了,可是它们的每个名字又像是睁开一只眼睛在看着你……它们等待着,直到你去把它们开启……在一个夜晚,当你经过困顿的旅途回到家中;在一个中午,当你不胜疲倦地离开人群;在一个早晨,当你昏昏然从睡梦中醒来——只有这时,你才……满怀着甜蜜尝试的享受性预感,走向橱边,上百双眼睛,上百个名字默默地、耐心地迎着搜寻的目光,宛如苏丹宫殿里的女奴在迎候自己的主人,谦卑地听候使唤。”
“书啊,你们是最忠诚、最沉默寡言的伴侣……你们的存在,就是永久的保存,就是无穷无尽的鼓舞……在那灵魂孤独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你们时时守护着,你们赐人以幻想,并在烦躁与痛苦中给人献上一刻宁静!每当灵魂被掩埋在凡生之中的时候……每当阴沉昏暗的时候,你们总是把我们内心的天空扩展到远方……一旦有心灵触摸了你们……你们的语句就会像驾着烈火的车辆,载着我们冲出狭隘境地,驶入永恒。”
可惜,这些滚烫的文字只能留在我的笔记本里。
唯有读书高
乡塾先生孔丘因为被广泛认为书教得好,被皇帝捧得老高,去他们家,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北宋皇帝赵恒说“书中自有千钟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五经勤向窗前读”,就有可能升官发财,出门有车马坐,找好看的老婆;北宋晚期的汪洙干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自然就成了自古以来无数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农民家过年,也会贴“耕读传家”的门联。“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白丁”就是目不识丁的人,是要被瞧不起的。学子们读书,几乎就是拼命。《战国策》记录苏秦读书打盹,就用锥子扎大腿,扎得血都流到脚上;《汉书》记录孙敬读书晨夕不休,半夜实在熬不住瞌睡,就用绳子一头绑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绑在房梁上,一打瞌睡头皮就吃不消;《朱子语录》记录两个宋朝学生去拜见当时的名流,见人家正在打坐养神,便恭立于门外的大雪中,等名流醒来时,雪已经下一尺深了。
古人读书,首在取功名。然而许多人得到梦寐以求的功名,一辈子也差不多走到了头。宋朝有个叫詹义的书生,七十三岁才考中秀才,媒人提亲,问他年龄,他只好自嘲:“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老婆也讨不到,别说出将入相了。
《三字经》说五代人梁灏,考状元时,殿试对答如流,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不如他:“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以此证明只要坚持,无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夺魁。可一个人八十二岁了,夺了魁又如何?《三字经》没有下文。
汪洙本人,自幼聪明好学,相传他九岁便能写诗,乡人传为“神童”。一生不仅淹贯博洽,熟悉经史,还写了不少浅显易懂、便于记诵的短诗,被汇编成《神童诗》,与《三字经》等同誉为“古今奇书”,成为训蒙主要教材。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等等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诗句,都在这本诗集里。但他自己直到将近七十岁才总算考中进士。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人们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考一个功名,有了功名却什么也干不了。何苦来哉。
好在汪洙后来做了一个州府学的教授,学生众多,有一府之望。一个读书人有这样的成绩,有没有虚头巴脑的功名,也就无所谓了。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大夫”,授正四品衔。对他本人而言,其实毫无意思。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
自古以来,关于读书的教训汗牛充栋,但也有不把这些教训太当回事的。
看到一则徐志摩关于古今读书之不同的高论:“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订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之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册,一年新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呐!你看我们念书的人可不着了大忙?眼睛只还是一双,脑筋只还是一副,同时这世界加快了几十倍,事情加多了几十倍,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徐志摩是才子。只有才子才有这样的落拓。经历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然后说:“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
与徐志摩同时代的林语堂对读书也取了一种散淡的态度: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称为清高”,倘若“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
“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书上怎么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事实上与学问无补……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书上讲有三大原因……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疟),这是书上所无的。”
“整个世界就是大学堂,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不如从校外所见所闻能得到的知识;只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一部字典在手,凭自修,什么学问都能学到。”
“出门、走路、看戏,也乱看乱学,文学乎,不文学也。”
“读书本来是至乐的事。